土地利用集约化对细菌、真菌和原生生物群落产生不同影响
导读
土壤微生物群落是维持植物生长和生产力的土壤养分循环的主要驱动因素。然而,仍缺乏土地利用集约化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影响的研究。本研究通过田间试验,调查了基于种植频率(连作、临时草地轮作、多年生草地)的土地利用强度变化对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及其共现网络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利用方式对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结构和组成有重大影响。草地和耕地种植存在明显的差异,两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分类群。临时草地和连作之间的微生物群差异最小,这表明临时草地之前的耕作制度的影响是持久的。与其他土地利用系统相比,土地利用强度还影响了多年生草地细菌共现网络的复杂性。同样,多年生草地微生物群内共现网络表现出更高的连通性。原生生物(尤其是Rhizaria)在土壤微生物组中占主导地位,在所有土地利用中,它们的关联数量都高于细菌和真菌。本研究结果为土地利用史会对土壤微生物组组成产生遗留效应提供了证据。无论土地利用类型如何,网络分析强调了原生生物在土壤微生物群落中的重要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予以考虑。综上,本研究为不同微生物群对农业集约化的不同反应及其与农业集约化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见解。
原名:Land-use intensification differentially affects bacterial, fungal and protist communities and decreases microbiome network complexity
译名:土地利用集约化对细菌、真菌和原生生物群落产生不同影响,并降低微生物群落网络的复杂性
期刊:Environmental Microbiome
IF:6.36
发表时间:2022.1
通讯作者:Laurent Philippot
通讯作者单位:法国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学
实验设计
结果
1.土地利用集约化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 为了表征连作(CC)、临时草地(TG)和多年生草地(PG)交替种植的土壤细菌、真菌和原生生物群落,利用DNA测序对土壤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进行了研究。细菌群落的α-多样性指数存在显著差异,连作和临时草地的OTU丰富度、Shannon指数和系统发育多样性显著高于多年生草地(Tukey’s检验,p值< 0.05,图S2)。相比之下,3种土地利用方式下,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的α-多样性指数基本一致。 利用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主坐标分析(PCoA)比较了群落β-多样性,结果表明,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按照土地管理方式进行了聚类,并且PCoA的前两个轴分别解释了37%、23%和34%的变异(图1)。PermANOVA进一步证实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显著差异(PermANOVA,p< 0.05)。然而,与多年生草地相比,连作和临时草地的细菌和原生生物群落结构更相似(图S3)。
通过16S rRNA基因测定总细菌群落丰度,在连作条件下显著低于临时草地和多年生草地(Dunn’s检验,p< 0.05,图2)。对于氮循环基因,nrfA在总细菌群落中的比例(nrfA/16S rRNA基因丰度)沿土地利用强度梯度增加(Dunn’s检验,p值< 0.05,图2)。此外,连作中AOB和nirS的百分比也较高,但其他氮循环相关基因没有显著差异(Dunn’s检验,p< 0.05,图2)。
图1 基于Bray–Curtis距离的PCoA分析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即连作(CC)、临时草地(TG)和多年生草地(PG)之间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变化:(a)细菌16S rRNA基因测序,(b)原生生物18S rRNA基因测序,(c)真菌ITS1测序。
图2 连作(CC)、临时草地(TG)和多年生草地(PG)土壤样品中总(a)细菌(16S rRNA基因)和(b)真菌(ITS)的丰度(平均值±SE); (c)氨氧化古菌(AOA)与氨氧化细菌(AOB)的百分比; (d)AOB、(e)和(f)细菌反硝化菌( nirK 和 nirS )、(g)固氮菌群( nifH )和(h)DNRA菌群( nrfA )在总细菌群落中的百分比。
通过Dunn’s检验(p<0.05)检验组间差异,条形图上方的不同字母表示土地利用之间的差异性。
2.鉴别差异OTUs
在所有样本中,优势菌门为Proteobacteria(33%)、Acidobacteria(21%)和Actinobacteria(17%)。原生生物以Cercozoa(45%)、Chlorophyta(15%)和Stramenopiles(14%)为主,而Mortierellomycotina (42%)和Sordariomycetes(22%)是最丰富的真菌类群(图S4)。三元图显示了最为丰富的OTUs的分布,所有样品中存在相似丰度的OTUs位于三元图的中心附近(图S5)。分析了不同用地类型之间差异丰富OTUs(16S rRNA为472个OTUs,18S rRNA为341个OTUs,ITS为218个OTUs),发现173个细菌OTUs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 0.00001)(图3a)。连作和永久草地之间的差异最大,共计166个差异细菌OUTs,其中101个OTUs在多年生草地中显著高于连作(图3b)。相反,连作与临时草地之间仅有28个OTUs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27个OTUs在临时草地中更高。属于Actinobacteria的OTUs受土地利用强度影响最大,从多年生草地到连作,相对丰度从7%下降到3%(图3a和图S4a)。对于原生生物,341个优势OTUs中有79个在三种土地利用方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图3c)。在多年生草地和连作之间,大多数OTUs的相对丰度存在差异(图3d),55个OTUs的相对丰度分别从32%下降至10%。受影响最大的OTUs属于Apicomplexa和Cercozoa(图3c和图S4b)。对于真菌群落,218个真菌OTUs中有95个受到土地管理方式的显著影响(图3e)。与细菌和原生生物的分布模式相似,多年生草地和连作之间的差异最大,多年生草地中有42个OTUs(如Agaricomycetes和Mortierellomycotina)更丰富,此外,48个主要属于Dothideomycetes的OTUs在连作条件下丰度更高(图3f和图S4c)。我们发现,在土地利用强度梯度上,只有4个OTUs (CC > TG > PG)显著增加,而12个OTUs(CC < TG < PG)均呈下降趋势。
图3 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微生物群落组成的三元图。
通过DESeq2识别了不同用地类型之间丰度存在差异的OTUs:(a)细菌;(c)原生生物;(e)真菌。轴线上每个圆圈的位置表示所示土地利用对每个OTU相对丰度的贡献。圆圈的大小表示所有样本中每个OTU的平均频率。颜色表示OTU在门或纲水平上的隶属关系。Upset图展示了不同用地类型之间丰度存在差异的OTUs:(b)细菌、(d)原生生物和(f)真菌。每个垂直线显示土地利用比较中共享或唯一的差异丰富OTU数量。
3.微生物群内的共现网络受土地利用的影响
利用最近开发的稀疏多元泊松-对数正态模型,从连作、临时草地和多年生草地土壤样本中推断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的微生物关联网络。利用网络大小(即节点数)、边、网络中的正负边之比、聚类系数(即节点的聚类程度)和平均度(即每个节点的平均边)来估计网络的复杂性(表1)。在细菌网络中,沿土地利用强度梯度,节点和边的数量逐渐减少(图4,表1)。然而,临时草地的正负关联比最高,是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的三倍(CC = 2.33, TG = 7.45和PG = 2.22),这是由于临时草地网络中负关联显著减少,负关联仅为13%,而连作和多年生草地分别为42%和45%。对于原生生物而言,临时草地的正、负边比率也较高,而其他网络属性在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相似(即节点数、边和平均度)(图4b和表1)。真菌网络在临时草地中表现出不同的趋势且复杂性更高(图4c和表1)。真菌网络在临时草地中也表现出正负关联比增加(CC = 3.20,TG = 5.21和PG = 4.50),类似于细菌和原生生物网络。草地轮作中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网络的聚类系数最高。
表1 微生物共现网络的性质。
图4 连作、临时草地和多年生草地中(a)细菌、(b)原生生物和(c)真菌群落的共现网络。
节点根据其在门和纲水平的分类学从属关系着色。节点的大小与每个节点的边数(即度)成正比。
边厚度与节点之间的相关性成正比,表示正相关关系(黑色,ρ>0.1)或负相关关系(红色,ρ<− 0. 1)。 4 微生物群之间的联系因土地用途而异 为了更好地理解土地利用如何影响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之间的联系,我们推断出每种土地利用包括所有三组的共现网络(图5a)。多年生草地中各类群的微生物网络最复杂,有586个节点和985个边,其次是临时草地网络,有517个节点和971个边,连作网络有445个节点和778个边(图5b)。相比之下,我们发现临时草地网络中的聚类系数和平均度更高,这表明节点的连接程度高于连作和多年生草地(表1)。组间网络的比较表明,46.3%的节点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共享。相比之下,三种土地利用的网络之间只有两个微生物边被共享(真菌-真菌和原生生物-原生生物)(图5d)。为了区分在不同土地利用中共同出现的类群的差异,我们比较了微生物类群内部和之间的正边和负边数量(图5c)。无论土地利用方式如何,微生物网络均以真菌-原生生物(28%)、原生生物-原生生物(27%)和真菌-真菌(24%)关联为主。细菌-原生生物和细菌-细菌组合分别只占边总数的11%和3%。而细菌-细菌关联的正/负关联比在临时草地上中最高(CC = 16, TG = 29和PG = 3.3)。3个类群间的关联主要表现为临时草地和多年生草地之间的联结数量较多。细菌-Rhizaria、真菌-Rhizaria、真菌-Alveolata和真菌-Stramenopiles关联就是如此(图S6)。
图5 (a)连作(CC)、临时草地(TG)和多年生草地(PG)三组微生物群落共现网络。节点根据其在门水平上的隶属关系着色。
节点的大小与每个节点的边数(即度)成正比。边厚度与节点之间的相关性成正比,表示正相关关系(黑色,ρ>0.08)或负相关关系(红色,ρ<-0.08)。(b)每种土地利用类型中每个微生物群的节点数。(c)每种土地利用类型和微生物组内组间网络的正(黑色)和负(红色)关联数量。(d)维恩图展示了跨组网络的共享/唯一节点和关联数量。
讨论
土地利用变化对地下生物群落影响的研究经常集中在细菌群落或真菌群落上。然而,原生生物作为细菌的主要捕食者,影响着土壤微生物组的组成。因此,需要采用更加全面的方法来全面了解土壤微生物组。对此,我们对基于种植频率的土地利用强度梯度下的土壤细菌、真菌和原生生物群落进行了比较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3个类群的β-多样性均受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连作、临时草地和多年生草地的群落差异显著。关于土地利用强度在驱动土壤原生生物方面的重要性知之甚少,研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气候因子被认为是原生生物群落组成的最重要预测因子,但我们的结果表明,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原生生物的影响程度与细菌和真菌群落相同。原生生物和真菌群落的α-多样性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均无显著差异,而细菌α-多样性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连作和临时草地的细菌α-多样性高于多年生草地。与本研究结果一致,之前的研究发现,土地转变为农业用地增加了细菌多样性。这可能是由于这些系统中植物群落的轮作导致土壤养分通过根系分泌物和作物残体的多样性增加,最终增加了细菌多样性。这与本研究中观察到的长期草地和连作制度下土壤有机质(SOM)生化性质的差异相一致。氮循环群落(即硝化菌、反硝化菌和DNRA菌)的相对丰度在连作中最高,说明土地利用可能是这些功能群的驱动因素。因此,以往的研究报道了土地利用对AOB和DNRA细菌相对丰度的显著影响。然而,由于参与氮循环过程导致氮损失(反硝化和硝化)以及氮滞留(DNRA)的微生物群落在轮作中富集,需要进一步确定无机氮在这些系统中的去向。 为了确定土地利用史(即连续种植后再进行3年的草地轮作)的潜在遗留效应,在草地轮作周期结束时,采集所有土地利用的土壤样品。在不受土地利用史影响的情况下,临时草地和多年生草地的微生物群落特征应当比连作更为相似。临时草地和连作的群落结构差异最小,说明在草地轮作之前的种植制度对群落结构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前人的研究已经调查了土地利用史对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发现遗留效应的持久性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过去的耕地对森林微生物群落造成了长期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农业废弃后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对这些长期影响的一种解释是,土地利用史导致了土壤性质的变化,如C和N含量或pH值,这些是土壤微生物群落的重要驱动因素,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恢复。Crème等人观察到,尽管在轮作期间插入了3年的草地轮作,但土壤有机质的生物地球化学特征更接近连作制度,而非永久草地,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一致。此外,植物种类还可以通过各种过程影响不同的土壤微生物群落,并在后续的植物群落中产生可检测到的残留,因此也解释了草地轮作与连作的相似性。总体而言,我们发现,连作历史至少在三年期间影响着微生物群落组成,这突出了在评估土地管理方式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土地利用史的作用。当考虑到土壤群落的这种变化会反过来影响后续的植物群落,这一点更为重要。 由于多年生系统和一年生系统在生态进化动力学上的内在差异,可以假设植物-土壤反馈可以导致永久草地中更复杂、关联更紧密的生态网络。然而,在分析各类群(细菌、原生生物和真菌)的微生物共现网络时,只有细菌网络更加复杂,随着土地利用强度降低(即从CC到PG),细菌OTUs之间的节点数和边数逐渐增加。这与前人研究发现草地细菌网络复杂性高于种植系统的结果一致。有趣的是,多年生草地的细菌多样性也是最低的,这表明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不一定反映微生物网络的变化。与之前的研究表明农业集约化降低了真菌网络复杂性相比,我们发现临时草地的真菌网络复杂度高于多年生草地和连作系统。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Banerjee等人对根系相关真菌进行了监测,而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土壤群落。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原生生物群落结构和组成的差异并没有反映在群落网络的复杂性上。而在边类型上,我们发现临时草地中微生物群落的正-负关联比都有所增加,说明土壤微生物之间的正相关性得到了促进。这可能是由于临时草地与作物轮作交替时生态位分化增加,导致微生物物种间竞争减少。相反,种植系统中正-负比的降低表明微生物类群间的合作建立效率较低,而不是竞争加剧。此外,之前的研究表明,群落均匀度的差异也可能影响正关联百分比,因为丰度相对较低的类群倾向于造成更多的负关联。无论如何,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解释共现网络中的这些变化是由生物相互作用引起的,还是由三种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环境条件的差异引起的。 最后,本研究分析了包含三组微生物的网络,以获得对于土壤微生物组沿土地利用强度梯度变化的整体理解。与细菌网络相似,我们发现草地群落间网络的复杂性更高,这支持了我们的假设,即多年生系统导致微生物网络连接更加紧密。这种复杂性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细菌和原生生物节点以及细菌-细菌、原生生物-原生生物和细菌-原生生物关联数量的增加,尽管与细菌相比,原生生物的个体网络在土地利用之间相似。虽然近一半的域间网络节点相似,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连接明显不同,表明微生物相互作用比群落结构对土地利用集约化更为敏感。考虑到最近的研究表明生态系统功能可能与微生物网络复杂性有关,土地利用管理影响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关联是很重要的。无论土地用途如何,原生生物在种群间网络中占主导地位(图5b),尤其是与细菌和真菌高度相关的Rhizaria(Cercozoa)。虽然当生境过滤作用很强时,共现网络会受到“欺骗性”的影响,但它们也可以再现微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可能的相互作用。虽然不是所有的原生生物都以其他生物为食,但它们是细菌的主要消费者。然而,我们发现原生生物(Rhizaria、Amoebozoa和Stramenopiles)与真菌之间的负相关比原生生物与细菌之间的负相关更多。因此,最近的研究表明,以真菌为食的原生生物可能同样重要。另一方面,一些真菌已经发展出了诱捕结构,如粘附孢子、菌丝,以捕获原生生物等土壤微生物。真菌也可以是原生寄生虫,例如阿米巴原虫吞食孢子或分生孢子,导致其死亡。这些捕食/寄生相互作用可以解释我们在研究中观察到的真菌和原生生物之间的一些负相关关系。
结论
在不同土地利用强度下管理的长期田间试验中,通过对细菌、真菌和原生生物群落的整体微生物组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土地管理只影响细菌群落的α-多样性,而在连作制度下增加了多样性。然而,我们发现所有群落的结构和组成都随着土地使用而发生了明显变化,特别是在连作和多年生草地之间。此外,本研究结果表明,种植对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遗留效应在临时草地种植三年后仍然持续。这突出表明,先前的土地利用可以为塑造当今跨领域的多种微生物群的群落。多年生草地系统导致了更复杂的细菌和域间网络,这可能意味着微生物对生态系统多功能性的贡献。域间网络还揭示了原生生物作为所有土地利用类型土壤微生物群落网络中的关键分类群的主要作用。未来的研究需要验证原生生物在形成土壤微生物群落中的重要性,直接通过生物相互作用和/或间接通过非生物因素的变化。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精彩评论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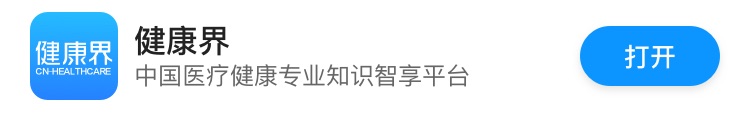




 打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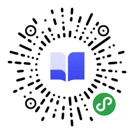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