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颗粒冷冻电镜之父”; Joachim Frank 82岁生日演讲 | 水木视界iss.29
祝冷冻电镜之父Joachim Frank
82岁生日快乐!
约阿希姆·弗兰克,德裔生物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生物化学、分子生物物理学等。
1975年到2008年间,弗兰克教授完善了电子显微镜图像处理的单颗粒算法,发明了SPIDER软件,该软件至今为全世界上百家实验室广泛使用。弗兰克教授应用冷冻电镜和单颗粒技术,在解析原核和真核细胞核糖体结构和功能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2017年10月,弗兰克教授与雅克·杜波谢、理查德·亨德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们在“冷冻电镜用于生物分子结构的高分辨率解析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2022年9月4日,弗兰克教授在国际研讨会后发表了生日演讲,庆祝他80,81和82岁的生日。
本期水木视界对约阿希姆·弗兰克教授的生日演讲进行翻译,期望更多冷冻电镜领域的同僚们能够从这位传奇冷冻电镜之父的言语间获得一些启迪。
Copyright © Joachim Frank
"I can tell you that, it all started with a kick." —Joachim Frank
致我的朋友、学生和同事们,
50年前,我不曾想象自己的梦想会在有生之年得以实现:我的那些研究,和我在编译计算机程序上花费的大量时间,孕育出了一项强大的结构生物学新技术,这种技术正在横扫世界,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那些形成生命结构分子的细微运作,研究病毒与人类受体的互动方式,并进而找到病毒进入细胞的途径。
196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接触到分子生物学领域(那时你们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出生)。当时我23岁,在弗莱堡大学获得了物理学学士学位,并刚刚搬到慕尼黑,开始撰写我的硕士论文。重要的是,除了高中学过的基础课程外,我对生物学一无所知。
犹记得在年幼时的暑假期间,我坐在我父母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魏德瑙的房子后院里,那里是我的故乡。不远处是我们的阳台,八岁时,我在那里做了我的第一个“科学”实验。在1964年的夏天,我坐在同样的地方,尝试着拆开一个新寄到的包裹,并期待着即将由德国学术奖学金基金会举办的一系列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旨在将不同学科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藉由学科的交叉,激发出一些前沿的创新思想。我报名参加了关于分子生物学的研讨会。
在当时,分子生物学正在逐渐被定义为一个领域。事实上,这个词在1954年左右才被创造出来,它将生物学的最终目标概括为"对分子及其相互作用的研究"。在五年后,也就是1959年,《分子生物学》期刊得以成立。分子生物学的子领域"分子遗传学"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在遗传学中,遗传的基础可以通过体内特殊分子的作用来解释。其中,最重要的便是DNA,遗传的物理基质。
至于那天我在后院打开的快递包裹里有什么?是一些关于分子遗传学的开创性文章的重印本。其中有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1953年发表的关于DNA结构的《自然》论文。这篇论文的结尾有一句著名的,却轻描淡写的话:“不出所料,我们此前所假设的特定配对立即表明了遗传物质具有潜在的复制机制。”
"It has not escaped our notice that the specific pairing we have postulated immediately suggests a possible copying mechanism for the genetic material."
—James Watson & Francis Crick
我还记得当时读到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一个基因一个酶”假说,于更早的1945年提出:这个假说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每个基因只负责编码一种且只有一种蛋白质。
在我终于领悟了分子遗传学的基础概念时,我感到兴奋异常,这个概念现在被定义为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教条”:这是由弗朗西斯·克里克创造的术语。如同许多高度情绪化的时刻一样,比如1969年的登月,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船的爆炸,或2001年9月11日双子塔大楼的倒塌,在理解一个开创性事件的那一刻,我所处的视觉场景就像照片一样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中:我坐在涂有白色油漆痕迹的木椅上,地面洒满了白色的石英砂砾(我父亲有每周六下午耙地的习惯),阳光照射在我祖父母于1905年建造的红砖家宅的屋顶上。那是一个突然的、瞬间的觉醒时刻,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概念,格雷戈里·孟德尔关于特征遗传的定律、生殖、细胞分裂、蛋白质的合成...所有的概念都汇集在一个宏伟的蓝图中,它们全部都联系在了一起。
回顾过去,我认为我的科学生活可以或多或少地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想法的大杂烩”是对许多想法的漫无目的的探索,允许它们在我头脑中相互碰撞。我对我的研究不设限,研究的内容也没有边界。初识电子显微镜时,它和生物样本是水火不容的。当纯粹的物理学与混乱的生物学相遇,许多想法都因不够成熟而消散了。我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在科学领域有所作为。
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尤里卡!(古希腊语:我明白了!)”,在这个阶段,我有了一个固定的研究思路:依靠溶液中的单分子集合进行结构解析,这在当时是相当反常的。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编写程序上,这些程序令我日思夜想,寝食难安。我生活在了我的程序中,这就像一个建筑师,不断地建造和改变他注定要居住的房子。幸运的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一些同事和合作者,包括今天在这里的马丁·凯瑟,他们给予我支持,使单颗粒概念的首批证据得以诞生。
然后是第三阶段“豚鼠的核糖体”。作为新晋的研究员,在许多优秀学生的帮助下,我能够非常详细地开发单颗粒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偶然地使用豚鼠的核糖体分子,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许多与我合作的核糖体生物化学家制作了样品,并提出了一些希望我能回答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我成为了一名结构生物学家。
第四阶段“登峰造极境”,也就是当下,我看到蓬勃发展的单颗粒技术在许多团队的手中绽放,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完美程度,并欣慰地知道我的想法最终助力于许多科学家们成功取得了向往的奖项。但在我所有的幻想中,我没有预料到会在82岁生日那天,被我的许多学生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科学家们包围,并收到如此多的赞美。
请允许我多描述一些关于“尤里卡”阶段的细节:单颗粒重建,如果一个分子没有被结晶,我们怎么能观察它的结构?这个反常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这一切都始于物理意义上的一“踢”。
1969年,在我开始在慕尼黑跟随沃尔特·霍普从事博士工作的一年后,我认识了波兰教授安东尼·费尔蒂诺夫斯基。他是一位难民,却在电子显微镜方面有一些经验,霍普同意在实验室里给他一个临时职位。费尔蒂诺夫斯基博士是一个高大的人。他嗓门极大,很有主见,而且相当烦躁。他的牛脾气影响了他所拍摄的显微照片的质量,因为他在实验过程中经常会习惯性地踢一下桌腿,这导致照片往往是模糊的。
碰巧的是,当时一种新的分析方式正在流行:光学衍射。当把记录在胶片上的电子显微照片放入平行的激光束中,通过透镜进行聚焦,就会看到一个衍射图案。它通常会显示出衬度传递函数的特征,即所谓的索恩(Thon)环的形状。这些环是以弗里茨·索恩的名字命名的,他是在1964年首次描述这类图案的科学家。当我把费尔蒂诺夫斯基博士的显微照片放入激光束中时,一种奇怪的叠加图案出现了:它看起来就像索恩环被放在铁栅栏后面。在我的认知里,这些栅栏被称为杨氏条纹。
这个奇怪的图案一下子揭示了实验的许多重要信息:第一,衬度转移函数。第二,图像在曝光过程中因费尔蒂诺夫斯基博士的踢腿而。第三,电子显微镜的分辨率,这可以通过能看到多远的条纹来进行判断。但最重要的启发是,我意识到有可能将两幅有噪声的图像中显示的分子对准,在物体的尺度上,实现3Å或更高的精确度。(为了非专业人士能够理解,1Å是0.0000001毫米)
我的第一篇论文得以完成,这篇论文发表于1969年。令我惊讶的是,我的导师,霍普博士并不希望他的名字出现在论文上,并拒绝签名。他希望我作为单一作者得到所有的荣誉。
由此,其他的一切都随之而来。有时我会突然想起费尔蒂诺夫斯基博士,他还好吗?还会在做实验的时候踢一下桌腿吗?
我知道,许多学生和年轻的研究人员都希望能得到一些提示,指引他们如何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例如,在2018年访问我的母校弗莱堡大学期间,我被要求给学生做一个题为“如何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演讲。
回顾过去,我发现我的成功伴随着许多偶然性,寥寥数语并不足以描述。例如,费尔蒂诺夫斯基博士的踢腿效应。如果一定要我给出一些建议的话,这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周边视野”。留意狭窄的视野之外出现的一些暗示。实验中的每一个意外结果都可能有一个独特的解释,涉及一个新的概念,或是一个新的机制。有时,通过思考完全不相关的东西来克服障碍,甚至可以让思绪飞向科学之外。用理查德·费曼的话说:“以最无纪律、最不敬业和最原始的方式,努力研究你最感兴趣的东西”。
“Study hard what interests you the most in the most undisciplined, irreverent and original manner possible.”
—Richard P. Feynman
而且一定要有情感上的支持,以弥合大量的不成功、实验失误和其他挫折。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我妻子卡罗尔的支持,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她对我的支持风雨无阻。
再次祝愿Joachim Frank教授82岁生日快乐!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精彩评论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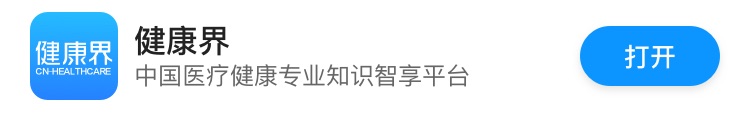




 打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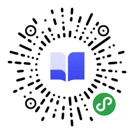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