泌尿外科的传奇(5):生活中有一种很大的诱惑力,就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而不是出于成功的希望。
被《加拿大泌尿外科杂志》邀请为这个系列做出贡献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将自己视为传奇是很困难的,有些人可能会说危险。看看以前的贡献者 - 真正的传奇 - 让我希望编辑没有犯错误。这是一个反思我的职业生涯如何发展的机会,以及我为泌尿外科领域留下了哪些成就,这给了我很多。这是一个机会,首先向我的导师致敬,没有他们,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其次,为团队科学辩护:我相信我的职业生涯证明了一个人可以从团队科学中做出什么贡献和获得对双方都最好的东西。當然,當我和妻子安托瓦內特(Antoinette)、我的妻子和兩個小兒子一起走過都柏林的停机坪,在去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進行泌尿外科住院醫學住院醫學的途中,我無法想像大約40年後,我會有幸寫下這本書。在学校时,由于我父亲的职业,人们认为法律职业就在我面前。当我听说我的祖母死于乳腺癌时,这一切都改变了。法律走了,医学在招手,我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学校观看橄榄球比赛时;谁说看足球不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消遣?
1964年,我和其他250名有希望的人一起进入了都柏林大学学院的医学预科。第一天,所有4英尺10英寸的克劳利博士,被亲切地称为"马"克劳利博士进入礼堂,站在讲台后面的一个盒子上,说:"同学们,看看你们右边的人,看看你们左边的人,但不要太喜欢他们,因为你们中的一半人明年就会走了。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2年后在都柏林的圣文森特医院开始了我的临床轮转。在这里,我受到了两位泌尿科医生弗兰克·达夫先生和丹·凯利先生的影响。达夫先生让每一次手术看起来都像是组织平面在做这项工作。在他们之间,泌尿科患者和护理人员之间,做出了决定:它必须是泌尿科。在当时的爱尔兰,泌尿肿瘤学没有这样的专业;事实上,这片土地上只有12名泌尿科医生。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在杜克大学的居留权,为此他们帮助我写了我的前两篇论文。
全家于1974年6月抵达杜克大学。杜克大学泌尿科,实际上是整个杜克大学学术机构,让我看到了学术泌尿外科以及它可能是什么。我突然成为一个大型协调努力的一部分,该努力由亚专科医生组成,作为一个团队工作。卓越,机会和同志情谊比比皆是。我的三位住院医师乔治·海姆斯特里特(George Hemstreet)、豪尔赫·洛克哈特(Jorge Lockhart)和查尔斯·布伦德勒(Charles Brendler)继续担任泌尿科主任。乔治·韦伯斯特(George Webster)重写了关于女性泌尿外科的书,而马斯顿·莱恩汉(Marston Linehan)则在NCI经营泌尿外科分支,并解开了肾癌的分子奥秘。一个人怎么能不在这些环境中茁壮成长呢?我有多幸运,我的部门主管格伦博士觉得美国毕业的泌尿科医生太多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保持居住权的同时,他请来了三名外国毕业生。Glenn博士是一位出色的头脑,泌尿科主任,院长,大学校长和癌症中心主任。他对住院医生的支持是传奇性的,他对泌尿科的热情也是如此,尤其是杜克泌尿科。它具有传染性。他教導我們去思考,去評估,然後去做,並且已經做過,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在我们回国前四个月,爱尔兰的工作失败了。格伦博士提出在我们解决问题的同时支持这个家庭。想想看,他绝对不欠我们任何东西,他给了我一个很棒的训练。它向这个男人说话,但也向我和我的家人在这个伟大国家的40年中所获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我们的困境,不是最后一次,当另外两位导师来拯救我们时,我们的困境得到了解决。指导我住院医师的David Paulson博士帮助我为爱尔兰的学术生涯做准备。他教我如何写论文。第一个我认为他让我修改,我认为他们在评论中称之为"重大修订",大约十几次。这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教训,遗憾的是,你并不总是遵循,你可以帮助某人实现他们的目标,但你不能为他们做他们的工作。因此,随着爱尔兰迅速而悲伤地消失在后视镜中,大卫将我和我的下一任导师卡尔·奥尔森博士固定了下来。1977年6月,全家驱车前往波士顿,在波士顿大学担任第一个学术职位。由于计划的突然变化,我没有医疗执照,也没有房屋的首付。卡尔什么也听不到,但他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就借给我们波士顿家的首付。我当然不想毁掉卡尔有时有点粗鲁的名声,但这只是他赋予我和许多其他人的众多行为中的第一个。总是没有大惊小怪,总是好像这是正确的事情,实际上是唯一要做的事情。在B.U.,Carl开始了我的研究兴趣,研究雄激素受体。我有时间,因为我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拿到考试和执照。我利用自发性肾癌大鼠模型扩展了我的研究。在这里,我学会了制定研究计划,获得资金,并建立必要的团队。
我职业生涯的下一个成长是当Olsson博士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担任泌尿外科主任时。我和他一起去了,全家人在拉奇蒙特开了一家店。卡尔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增加泌尿科研究,这是高度的信任。卡尔是一位出色的创新外科医生;我相信他在该国的一位女病人身上做了第一个原位的kock袋。他有一种奇妙的能力,可以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什么会真正产生影响:他增加了我的研究工作,他聘请了Ralph Buttyan博士,直到今天,他仍然是前列腺癌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我的基础科学研究培训始于正在研究流式细胞术的细胞生物学家Arlene Deitch博士将我置于她的翅膀之下 - Arlene在接下来的26年中继续这样做 - 而Carl则提供种子资金。我们在癌症研究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在3年后发表,其中我们利用DNA分析来尝试预测我从B.U.带来的大鼠肾细胞模型中的化学敏感性。我们很快进行了利用流式细胞仪和DNA分析进行前列腺癌和尿路上皮癌的研究。在Buttyan博士的帮助下,前列腺癌的生物医学研究仍在继续。当我们到达哥伦比亚大学时,哈里斯·纳格勒(Harris Nagler)博士一直作为不孕症患者留下来 - 我的到来一定有点震惊。他对自己计划中的改变非常亲切。正是通过哈里斯,我在波士顿所做的不孕不育工作被转移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斯做了一些杰出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关于扭转对未来生育能力的影响。他是一位好朋友,在哥伦比亚的早期非常有帮助。多亏了这些,以及其他人,我在纽约获得了管理经验,并建立了4年多的简历。
我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知之甚少,当他们打电话给他们空缺的泌尿外科主席时。这是纽约一个寒冷的二月天。我从未忘记第一次飞往萨克拉门托的航班(大学在戴维斯,而医院在萨克拉门托的路上12英里),当我们降落在太浩湖和山脉的白雪皑皑的山脉上时,真的很棒。六个月后,全家安顿下来,我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担任泌尿外科的第二任主席。在接受这份工作之前,我的困境是戴维斯需要建立一个临床项目,并开始他们的研究项目。院长告诉我,我需要在戴维斯大学开始研究项目,因为人们不在萨克拉门托做研究。另一个小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招聘博士学位。在我回到纽约时,她向阿琳·戴蒂奇(Arlene Deitich)描述了这一切,她宣布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她和她的丈夫沃尔特将离开纽约,他们已经生活了62年,和我们一起来。他们俩是多么慷慨,多么信任他们,对我和戴维斯的泌尿科部门以及整个大学来说是多么幸运。
我们在萨克拉门托的实验室位于一座古老的州立展览会场大楼内。我们购买了第一台库尔特流式细胞仪机器 - 这就像买了一辆高档跑车。然后,我们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泌尿外科研究计划。我们的第一笔NCI资金被授予用于研究前列腺癌中的DNA流式细胞术,我们的第二笔资助是NCI小组的一部分,该小组评估流式细胞术在管理尿路上皮癌中的作用:因此开始了泌尿科研究实验室。NCI告诉我们,随着DNA授权的首次更新,进入下一个阶段,将意味着扩展到前列腺癌的分子生物学领域。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另外两个人也加入了这项工作:Paul Gumerlock博士,博士当时与Frederick Meyers博士一起工作,当时他是一名年轻的医学肿瘤学家,现在是我们的执行副院长。
在前列腺癌中,实验室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专注于了解microRNA在CaP中的功能作用。我们是最早发表关于改变CaP中microRNA的功能重要性的人之一。在前列腺癌的DNA流式细胞术和肿瘤抑制器工作开始之后,我们与密歇根州的Syders博士和Lee博士,丹佛的Gary Miller博士和华盛顿特区.C的Jackson博士联手提交并获得了前列腺癌P01的资助。这是我第一次进入真正的团队科学领域。没有大家的投入,这就不会发生。此时受到热烈欢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入了SWOG,Meyers博士和我加入了泌尿外科工作组,受到当时的领导者David Crawford博士和Derek Raghavan博士的欢迎。这是我下一次团队科学的经历。我后来成为ucd UCOP资助的PI和相关科学计划的最初领导者。多年来,我有机会与41位不同的作者一起发表了大约14篇不同的论文,并获得了两笔资助。对于任何年轻的学术泌尿肿瘤学家,我强烈建议加入和参与合作小组。它帮助你学习,提供机会,并带来许多奇妙的友谊。
泌尿科临床项目的发展还需要招聘新的教师,并专注于发展一个子专业部门。出于许多原因,我相信神经泌尿学是开始的地方。保尔森博士再次向我求助,向我介绍了安东尼(托尼)·斯通博士。托尼从英国来到杜克大学,与乔治·韦伯斯特(George Webster)一起担任研究员,并作为住院医师留下来,因此他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普通外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和神经泌尿科医生: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广泛经验。托尼在我来的第二年加入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并在女性泌尿科,失禁和神经泌尿科方面建立了一个出色的项目。在早期的日子里,他还开始了我们的腔内泌尿外科项目。我们很幸运能有一位杰出的教师加入。
1996年,下一个重大变化发生了。James Goodnight博士是一位外科肿瘤学家,他创办了我们的癌症中心,后来担任外科主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把P01组装在一起,我成为我们癌症中心的主任。当时,我们每年有1700万美元的资金。在该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建造了建筑物,癌症病毒学,前列腺癌酪氨酸激酶功能专家Hsing-Jien Kung博士从凯斯西部癌症中心招聘成为我们的基础科学创始副主任;David Gandara博士是肺癌,临床试验方面的国际专家,也是SWOG肺委员会主席,成为我们的临床研究副主任。经营癌症中心是团队科学的终极:我们有285名成员,他们共同导致癌症中心在2002年获得指定。在接下来的8年中,我们的资金增加到每年超过1亿美元,并于2012年成为该国第41个NCI指定的综合癌症中心。是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除了照顾病人之外,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满意的了。这就像华尔街,你做了最后一个季度吗?您未来的投资组合是什么?
当我接管癌症中心时,医学院同意我可以再聘请一名泌尿肿瘤科医生。我很幸运地说服了克里斯·埃文斯博士加入我们。他是一个了不起的新兵。克里斯证明了"三重威胁"仍然存在。当我们在达拉斯的AUA交谈时,在他来之前,克里斯问我为什么想让他来。我说,当时机成熟时,我希望他接管泌尿外科。我感到自豪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2006年。在克里斯的领导下,该部门蓬勃发展,在该国任何泌尿科的拨款资金方面上升到第二位。对克里斯来说,剩下的唯一考验就是在我进入我的溺爱时与我打交道。
这是一个40年前离开爱尔兰的家庭。这是一个一直活在美国梦中的家庭。我的妻子安托瓦内特(Antoinette)花了25年多的时间帮助萨克拉门托的无家可归者。不久前,我正在进行搜索,候选人提到她用谷歌搜索了我。她说,虽然我的职业生涯看起来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但我的妻子似乎更有趣,我最近即将上任的院长也重复了这种情绪。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三个儿子用三个了不起的儿媳妇丰富了这个家庭,他们一起给了安托瓦内特和我六个光荣的孙子,我的母亲称之为我们的新人质财富。那么,在那些职业生涯开始时,我能给那些人什么建议呢?我已经谈到了导师的重要性和我对团队科学的支持。一个人职业生涯的成功并不依赖于才华——一种供不应求的商品——而是依赖于聪明的工作。我们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才能,我们所能要求的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个人分配。最后,我认为生活中有一种很大的诱惑力,就是出于对失败的恐惧,而不是出于成功的希望。我鼓励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出于成功的希望而做事要好得多。因此,在一天结束时,当安托瓦内特和我反思我们的好运时,多亏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可以溜到de Vere的爱尔兰酒吧,也许可以安静地喝酒。如果在城里,请来加入我们。
Ralph W. de Vere White, MD 萨克拉门托, 加利福尼亚州, 美国
© 加拿大泌尿外科杂志™;21(2);四月 2014 7178
Legends in Urology v21I02
de Vere White W. Ralph, ;
Codman-Radke Chair in Cancer Research, Sacramento, CA, USA
LEGENDS
Apr 2014 (Vol. 21, Issue 2, Pages( 7176 - 7178)
PMID: 24775566
Ralph W. de VereWhite,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综合癌症中心医学主任 癌症项目副院长 泌尿外科科德曼-拉德克癌症研究系杰出教授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精彩评论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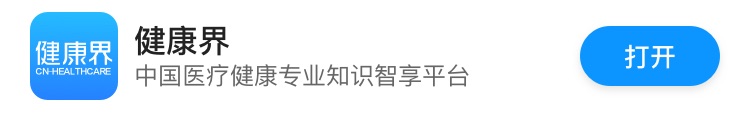




 打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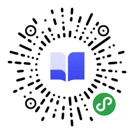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