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show!中国医院管理案例评选,医院卓越管理实践大秀场。
点击查看
编译:微科盟郝恬,编辑:微科盟木木夕、江舜尧。
微科盟原创微文,欢迎转发转载,转载须注明来源《微生态》公众号。
导读
人类肠道微生物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它是具有抗生素耐药性基因(ARGs)的细菌的储存库。然而,抗菌素耐药性(AMR)以及早期如何患有AMR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不清楚。
在生命的最初几年,新出生婴儿的肠道微生物群落是动态的。变动中的肠道微生物被破坏会增加后期患一系列疾病的风险,包括哮喘和过敏。最近我们描述了1岁时未成熟的肠道细菌组成如何与后期的哮喘和过敏发生关联,以及1岁时的微生物组成如何预测5岁时的哮喘。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命最初几年对肠道微生物群的适当成熟至关重要,这对宿主代谢和免疫有进一步的影响。
婴儿肠道中正在发展的微生物很容易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例如分娩模式、饮食、家庭和抗生素。微生物和抵抗体与导致AMR的基因息息相关。所以,除了抗生素药物的摄入之外,大量的环境因素能影响婴儿肠道中的ARGs。暴露的环境与婴儿肠道微生物的联系已经被很好的证实,出生后第一年肠道微生物的成熟度和组成不充分与后期哮喘的发展有关。然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儿童早期肠道微生物的耐药性,肠道微生物的结构和成熟度与后期哮喘风险之间的联系也没有被探索。
在这里我们提供了来自哥本哈根哮喘前瞻性研究所2010年出生的662名健康儿童在1岁时肠道微生物中ARGs的分布。通过采用大量的方法,我们调查了这些基因与环境、微生物成熟度、与哮喘相关的婴儿肠道细菌组成之间的联系。这些发现加深了我们对早期AMR的理解,并对减轻其传播有关键影响。 原名:The infant gut resistome associates with E. coli, environmental exposures, gut microbiome maturity, and asthma-associated bacterial
译名:婴儿肠道耐药性与大肠杆菌、所处环境、肠道微生物成熟度和与哮喘相关的细菌组成有关
期刊:Cell Host & Microbe
IF:21.023
发表时间:2021.6.9
通讯作者:Johannes Sørensen
通讯作者单位:哥本哈根大学微生物科生物学系

在COPSAC2010的母婴队列中,共获得662名一岁婴儿的粪便样本,并用鸟枪法宏基因组学测序。我们在这组婴儿中检测到了409种ARGs。这些基因对34种药物具有抗药性,其中167/409种(40.8%)基因包含多重抗药性。所有的孩子肠道中都至少有一种具有多重抗药性的基因(图S1A),即使这些儿童从来没有亲自服用过这些药物。在这些肠道微生物中,WHO将这些耐药基因分为重要、高度重要和极其重要三类。这表明了耐药性与住所、母体遗传和暴露的环境之间的联系。到目前为止,四环素和氟喹诺酮类的ARGs最常见,其次是培南、头孢菌素、大环内酯类和头霉素(图1A)。对于多粘菌素类药物,我们在5名儿童中检测到了新的耐药基因mcr-9同源物:五个氨基酸片段显示85%-100%覆盖,与mcr-9 100%同源。这些发现揭示了耐药性在婴儿之间普遍存在。当我们定义ARGs的功能和分布时,我们发现外排泵是最重要的耐药机制(图1B)。ARG丰富度明显呈现双峰分布(图1C),19种AGBs呈小峰,69种AGBs呈大峰(基于二组分的泊松混合模型)。所以基于ARG丰富度,所有样本可以被成分两组(图1D)。接下来我们研究了是否ARGs的丰度分布会像ARG那样呈现双峰分布。基于此,我们采用了一种叫“围绕中心点划分”(PAM)的方法。首先,样本之间Bray-Curtis 相异度基于每组ARGs的归一化丰富度计算。然后利用这些数据计算基于ARG组成的种群中不同聚类的最佳数量。聚类质量由剪影图(图1E)表示,K=2时聚类质量最高(0.35),表明这是最优的聚类数量。两个PAM聚类的分组与图1D的模式一致,聚类1和聚类2分别包含438和224个样本(皮尔逊相关系数,t = 54,df= 660,r = 0.9,p < 2.2e-16)。两组之间的序列覆盖率无显著性差异(t检验,t = -1.7,df = 454,p = 0.09,图S1B、S1C和S1D),证明测序深度不是决定其分组的因素。然而,正如非度量多维尺度(NMDS)图,这两个PAM聚类在基因谱(β-多样性)上不同(置换多元方差分析,R2=12%,图1F)。相比聚类2(n=224),聚类1的样本更丰富(n=438)(平均值,聚类1和聚类2对比;594对708,图1G),有更多样的ARGs(α-多样性)。此外,我们还发现了58个差异极大的ARGs,在聚类1和聚类2中丰度变化超过4倍,这58个ARGs都在聚类1中富集(图S1E)。这58种差异极大的ARGs对23种药物具有耐药性,其中最常见的是氟喹诺酮类和青霉类(图S1F)。为了确定这两种ARG PAM聚类是否由暴露的环境塑造,我们调查了兄弟姐妹的存在、抗生素的使用及频率,抗生素的使用时间、怀孕期间抗生素的使用、分娩方式、母乳喂养、家庭类型、生活环境、宠物的存在以及出生季节。在这些因素中,只有怀孕期间使用抗生素会造成聚类之间的显著差异,在PAM聚类1中,438名母亲中的45%(n=198)接受过抗生素治疗,而在PAM聚类2中,224名母亲中的33%(n=74)接受过抗生素治疗(费希尔精确检验, p = 0.0027,让步比 =1.67 (95%CI: 1.18–2.38))。
图1. 662名1岁儿童肠道ARG谱的特征和聚类分析(A)不同药物类别相关ARGs的丰度。(B)每种ARG的耐药机制,描述为检测到的所有ARGs的比例。(C)每个样本ARG丰度密度图。(D)样本中ARG丰度的热图。(E)使用不同数量聚类时与PAM聚类相关的平均剪影宽度。轮廓宽度表明了一个样本与它自己的星团相比与邻近星团的相似程度。高平均剪影值表明强聚类。(F)基于两个ARG PAM聚类中ARG丰度的Bray-Curtis不同矩阵的NMDS图。(G)两个ARG聚类的ARG丰度(a-多样性)和对数转换总ARG丰度。
为了确定造成ARGs双峰分布的影响因素,我们调查了两组聚类的细菌群落。每个聚类的细菌组成用MetaPhlAn 2.7.5统计。通过这个程序的分析,证实了细菌群落组成和ARGs分类之间的联系(相关系数r = 0.7798,p= 0.0001,图2A),表明有相似样本分类的细菌具有相似的耐药性。PERMANOVA测试(图2B)表明,在物种水平上,两个聚类的细菌群落(β-多样性)明显不同(p < 0.0001)。然而,两个聚类在α-多样性上差异并不明显(单因素方差分析, F = 4.3, p = 0.038,图2C)。这些结果显示,ARG组成在两个聚类之间的变化主要是细菌丰度之间的差异。为了确定这种模式的代表性细菌,我们分析了一个聚类相对于第二个而言过多表达的物种和类群。运用秩和检验,我们发现了5门/143种细菌在两个聚类之间有明显差异,在聚类1中2门/61种细菌表达较多,在聚类2中3门/61种细菌表达较多。在门水平上,聚类1中的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显著增多。在最丰富的30个物种中,有24个物种在一个聚类比另一个聚类更丰富。在列表(图2D)中,大肠杆菌和一些未分类的埃希氏杆菌属显著,这两种基因在聚类1中更丰富。聚类1的优势菌群为大肠杆菌,平均相对丰富度为8%,然而聚类2为0.2%。最后,我们运用随机森林法在多个分类水平上对细菌的重要程度进行排序。在每个水平上(门,纲和科),包含大肠杆菌在分类单元(分别为变形菌门,丙型变形菌纲,肠杆菌科)比其他分类单元更重要。这些结果指出大肠杆菌和一些未分类的埃希氏杆菌属在两个聚类之间的划分发挥了关键作用(图2E)。接下来,利用与大肠杆菌对应的组装基因组(MAG),我们定义了所有的来源于这个物种的ARG携带序列。在聚类1中,438样本中有289个序列被追踪到大肠杆菌(图2F)。其他聚类1的样本和聚类2的样本没有检测出大肠杆菌(图2F)。为了验证来自于大肠杆菌属的ARGs在聚类划分的重要性,我们从包含他们的样本中移除了它们。这导致了两个ARG聚类方差降低了10倍(16%到1.6%)(β-多样性, N聚类-1 = 289, N聚类-2 = 224))(图2G),聚类1 ARG丰富度显著降低,达到了与聚类2形似的水平(图2H)。这个巨大的下降反映出在聚类1中与大肠杆菌相关的ARGs的极端丰度:从这个聚类中几乎55%的ARGs是来自这个物种(图2I)。此外,来自大肠杆菌的序列负责了聚类1的所有58个差异显著的ARGs中94%的丰富度。在这些58个差异显著的ARGs中,来自大肠杆菌的占据了聚类1丰富度的67%-100%(图S2A)。众所周知,大肠杆菌在婴儿肠道微生物中所占的比例比成年人更大,婴儿体内的ARG丰富度似乎更可以被这种物种丰富度解释。为了调查两个ARG聚类大肠杆菌丰富度的动态变化,我们分别在1周(n = 527)、1月(n = 583)、1年(n = 623)、4年(n = 388),5年(n = 151)和6年(n= 350)时进行16S rRNA基因测序数据(n = 2622)。基于16S rRNA扩增数据,两组大肠杆菌的丰富度在1年龄的时候有显著差异,但在1周、1月、4年、5年或6年的时候没有(图S2B和S2C)。这表明在1岁时两组ARG聚类中大肠杆菌的丰富度更多地是被短暂或随机因素的影响-例如季节、抗生素暴露、微生物群落的环境动态监测,而不是长期或者永久的因素,如母体遗传或者宿舍遗传。此外,我们发现大肠杆菌的平均相对丰度在最小年龄时最高(1周:17% ±25.6%;1月:18%±26.8%),随后逐渐下降并趋于稳定(1年:6.8%±12.6%;4年:3.3%±8.3%;5年:2.8%±6.3%;6年:5.3%±12%)。这似乎表明,在生命的第一年,肠道抵抗体的丰度可能同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达到一个新的、较低的平衡。
图2. 两个ARG PAM聚类中的细菌种类概况以及大肠杆菌ARG在形成这两个聚类中的作用(A)普氏分析两个ARG聚类中抵抗体的组成和以MetaPhlAn为特征的细菌群落的组成之间的关联。(B)基于两个ARG PAM聚类中标准化细菌丰度的Bray - curtis相异度矩阵的NMDS图。(C)在两个ARG聚类中观察到的细菌丰富度(α-多样性)。(D)24个物种的相对丰度在两个聚类之间的差异。(E)细菌物种对PAM聚类分组的重要性。(F)662个样本中大肠杆菌的宏基因组分析。(G)从聚类1中去除大肠杆菌ARGs之前和之后基于Bray-Curtis 相异度矩阵的MDS图。(H)在含有和不含有大肠杆菌ARG聚类1中观察到的ARG丰度(α-多样性)(左)和对数变换总ARG丰度(右)。(I)聚类1中来源于大肠杆菌的所有ARGs的相对丰度(百分比)(n = 289)。(J)聚类1中大肠杆菌中58个差异显著的ARGs的相对丰度(百分比)(n = 289)。
为了鉴定婴儿肠道中来自不同细菌的ARGs,我们使用宏基因组序列追溯每个基因的来源。ARGs被追溯回208个物种,代表7个门(图S3A)。变形杆菌占据婴儿肠道微生物ARGs的大部分,尤其是肠杆菌科的成员,如大肠杆菌、克雷伯氏菌和肠杆菌,导致了大范围的感染。值得注意的是,大肠杆菌含有多达101种ARGs(图3A),占变形菌门ARGs的91%(图3B)。变形菌门的大量繁殖可以反应出肠道内的生态失调和功能变化。经过抗生素治疗后,已经观察到人类肠道微生物中变形菌门暂时性的大量增加,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损失。此外,变形菌门以通过偶联的方式将DNA转移到其他细菌而闻名。这与我们发现的ARG丰度与变形菌门之间的关系一致,并反映了变形菌门在塑造肠道菌群动态环境和肠道AMR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调查了每个人特有的ARGs的数量(图3C),变形菌门脱颖而出,有133种独特的ARGs(图3C),其中68个来自于大肠杆菌。这些来自于变形菌门不同寻常的ARGs主要与β-内酰胺抗性有关。在厚壁菌门中,检测到了61中独特的ARGs(图3C),其中大多数具有糖肽抗性(图S3B)。放线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有10种和9种独特的ARGs,放线菌门与氨基糖苷类抗性有关,拟杆菌门与β-内酰胺抗性有关(图S3B)。
图3. 1岁婴儿肠道的细菌种类和ARGs在门水平上的分布。(A)细菌种类的ARG丰度(外圈)和log转化的总ARG丰富度(内圈)。(B) 5个主要菌门和大肠杆菌中ARGs的总丰度。(C) 5个主要细菌门之间的重叠和独特ARG数的韦恩图。
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评估婴儿肠道中ARGs的分布受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表1)。ARG的β-多样性与抗生素的使用、频率、用过抗生素的间隔时间、兄弟姐妹、家庭类型、居住环境类型以及分娩方式有关(表1,PERMANOVAfor Bray-Curtis distance;p = 0.025、0.024、0.022、0.008、0.012、0.025、0.012、0.033)。然而这些因素只能解释ARGs变化的一小部分(R2值低于1)。而且,除了家庭类型和孕期抗生素的使用情况外,大多数因素对ARG丰度(α-多样性)没有显著影响(表1)(秩和检验;p = 0.0136、0.028)。住在公寓中儿童的ARGs平均数(58)比住在房子里(53)的更高。同样,母亲在怀孕期间服用抗生素的儿童的ARGs数量(57)比没有服用过的(53)更高。我们还比较了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ARG丰富度(表1)。抽样前6个月服用抗生素的儿童的平均ARG丰度显著高于抽样前6个月从未服用抗生素或服用抗生素时间超过6个月的儿童(Kruskal-Wallis检验,p = 0.026)。生活在城市的儿童的平均ARG丰度显著高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在以下条件下儿童肠道的平均ARG丰度也较高,但不显著:儿童频繁使用抗生素、儿童和孕妇使用抗生素、无兄弟姐妹,在冬季或春季出生,居住在公寓、剖腹产出生、家里养狗、家中无猫(表1)。此外,一些头孢霉素、四环素和硝基咪唑ARGs的丰度与兄弟姐妹的存在、住在公寓、住在城市地区和出生在冬季相关,如图S4A所示。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这些因素对整个肠道微生物群落(β-多样性)组成的影响(表1),发现兄弟姐妹的存在、家庭类型、生活环境和分娩方式有显著影响(PERMANOVA for Bray-Cutis distance,p=0.00033、0.00033、0.00033、0.002)。有趣的是,尽管使用抗生素对ARGs有显著影响,但似乎没有影响微生物群落的整体结构 (PERMANOVA for Bray-Curtisdistance,p > 0.05)。这表明,与其他环境因素同时影响ARG丰度和细菌组成的情况不同,抗生素暴露能够直接影响ARG丰度,而不影响总体微生物结构。可能的解释包括ARG通过水平基因转移在细菌之间转移,以帮助他们在抗生素暴露的环境中生存或选择携带ARG的亚种。相反,其他环境因素对ARG分布的影响可能是由宿主细菌介导的。与我们的结果一致的是,一些研究表明,不断扩大的城市化、生产模式和兄弟姐妹的存在对肠道微生物结构有明显的影响,住在公寓里对床上灰尘微生物有重大影响。城市化通常与室外微生物暴露减少和生物多样性下降有关。家庭类型可能与收入、卫生条件和居住区域有关,这些也会对肠道微生物群产生影响。剖腹产分娩会导致婴儿肠道微生物菌群失调,且通常与抗生素的使用有关。哥哥姐姐的存在可能会影响环境微生物群从生活环境转移到室内。抗生素对人体肠道微生物有短期的影响,但对AMR有持久的影响。然而,抗生素对肠道ARGs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未被探索。我们通过评估抗生素治疗后ARG丰度随时间的变化来对此进行研究(图4A)。肠道中ARG的丰度在抗生素治疗后的第一天是最高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逐渐降低趋于平稳 (皮尔逊相关系,t =3.1,df= 171,r =0.233,p = 0.002)(图4A)。这个趋势并不是被抗生素影响的大肠杆菌推动,当所有的大肠杆菌从样本中剔除之后依旧如此。抽样前2个月服用抗生素的儿童总ARG丰度显著高于从未服用抗生素的儿童(秩和检验,p = 0.05,图4B)。相比之下,在抽样前服用抗生素超过两个月的儿童与未服用任何抗生素的儿童之间的ARG丰度在总数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秩和检验,p = 0.77,图4B)。然后重复分析三种主要抗生素药物氨苄西林、青霉素和大环内酯类。为了减少不同抗生素药物类别对ARG存在和丰度的相互影响,我们只包括在第一年给予一次一种抗生素的儿童(n =180,图S4B),并且只检测了对该抗生素产生耐药性的ARG。在三大类抗生素中,取样前两个月服用大环内酯的儿童肠道与大环内酯相关ARGs的丰度明显高于未服用任何抗生素的儿童(图4C,秩和检验,p = 0.0),而氨苄青霉素和青霉素对婴儿肠道中各自相关ARG的总丰度没有显著影响。然而,抗生素可以对某些ARGs会产生一种长期影响,在四种主要抗生素治疗后,一些ARGs存在时间超过6个月,包括aadA3、dfr8、cmlA1、qacH、SAT-2、sul3、ErmX和OXA-85(图S4C)。图S5列出了在第一年对抗生素治疗丰富度差异显著的ARGs。总而言之,除了孕妇分娩40天之内使用抗生素之外,孕期使用抗生素并不影响婴儿肠道中ARGs的丰度(图4D)。抗生素治疗越接近分娩,儿童ARG丰度越高(Pearson相关,t = 2.2,df = 88,r= 0.231,p = 0.0278,图4D),这一发现可能与阴道微生物组转移有关。尽管之前的研究表明,母亲的抗生素可能会转移到母乳中,我们的结果表明,使用抗生素对1岁纯母乳喂养的儿童肠道中的ARG没有总体显著影响。然而,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大多数婴儿的肠道样本是在母亲接受抗生素治疗7个多月后采集的,这可能稀释了母乳介导的母亲抗生素使用对婴儿肠道耐药菌的影响。表1. 环境因素及其对ARGsα-多样性和总丰度的影响

图4. 环境因素对肠道ARGs的α-多样性、β-多样性和总丰度、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特别关注抗生素处理后。(A)自最后一次抗生素处理以来,log转化的总ARG丰度随时间的变化。(B)取样前不到两个月给予抗生素、取样前两个月以上或根本没有给予抗生素的儿童肠道中总ARG丰度的对数转换。(C)取样前两个月服用其中一种抗生素的儿童肠道中三组ARGs(氨苄西林相关、青霉素相关和大环内酯相关)对比未服用抗生素的儿童肠道中三组ARGs。(D)妊娠后期抗生素使用对1岁时ARG丰度的影响。
5 ARG聚类和ARG负荷与肠道微生物群成熟度和哮喘相关的细菌谱有关COPSAC2010出生队列研究旨在研究儿童哮喘,以制定循证的预防策略。因此,哮喘表型在该队列中得到了彻底验证。在之前的一项针对1岁时的微生物群落和5岁时哮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基于样本的微生物丰度(使用16SrRNA数据量化)构建了一个交叉验证的稀疏偏最小二乘(PLS)法模型。这项研究表明,哮喘母亲所生的儿童中,某些微生物组谱可预测5岁时的哮喘,曲线下的中位数交叉验证面积(AUC)为0.76。基于PLS模型的微生物每个孩子的1岁时的微生物群落富集样本,可以得出一个PLS分数,PLS的分数越高,证明患哮喘的风险更高。在这里我们改变了这项工作,去调查相同样本中ARG谱和与哮喘相关的细菌谱之间的关系(由PLS评分显示)。根据ARG PAM聚类结果进行PLS评分时,我们发现聚类1中的儿童的中位数评分高于聚类2中的儿童(秩和检验,P = 1.47e-14,图5A)。此外,我们发现ARG负载与哮喘细菌LPS评分呈正相关(Pearson相关,t = 10.4,df = 592, r =0.39,p <2.2e-16,图5B)。接下来,我们研究了如果从分析中移除了大肠杆菌,ARG聚类和哮喘相关细菌谱之间的关系是否还成立。为此,我们拟合了两个线性模型(图5C),一个以大肠杆菌的对数变换相对丰度作为自变量,另一个以大肠杆菌和ARG聚类的对数变换相对丰度作为自变量。在多元线性模型中,大肠杆菌的丰富度 (t检验,t =4.739,df= 591,p = 2.96e-06)和ARG聚类(t检验,t =2.172,df = 591,p= 0.0303)与PLS分数的变化显著相关,但没有观察到相互作用。在线性模型中,当大肠杆菌的丰度在两个ARG聚类中都被固定时,聚类1的PLS得分显著高(图5C)。这些结果表明ARG丰度与增加日后哮喘风险的细菌组成有关。ARG丰度本身并不被怀疑是哮喘的一个原因,但通过促进哮喘相关的细菌组成,它可能是一个间接的危险因素。这种关联可能与哮喘相关细菌中的ARG丰度有关,也可能与以下所示的较高ARG丰度导致的肠道成熟度较低有关。早期肠道发育不成熟会增加各种后期疾病的风险,包括哮喘。最后,为了描述高ARG丰度和1岁时肠道微生物成熟度之间的关系,我们采用了之前开发的模型,计算每个样本的“按年龄划分的微生物”Z评分(MAZ),值越高,说明肠道成熟度越高。该模型由1周,1月,1年的16S rRNA基因数据集练而成。我们发现,聚类1儿童的肠道微生物组更不成熟(秩和检验,p = 3.74e-06,图5D)。除此之外,高ARG负载明显与低MAZ分数有关((皮尔逊相关系数,t = 5.8,df= 592,r = 0.2322,p = 1.029e-08,图 5E)。与PLS评分一样,我们拟合了两个线性模型来研究ARG聚类是否与大肠杆菌的肠道成熟度有关(图5F)。在这里,我们发现大肠杆菌是肠道微生物群不成熟和两个ARG聚类之间关联的唯一因素。在多元线性模型中,大肠杆菌对MAZ分数有明显的影响 (t test,t = 2.2,df = 591,p=0.026,图5F),但当大肠杆菌在两个聚类间保持不变时,ARG聚类与MAZ评分之间没有关系(t检验,t = 0.519,df = 591,p= 0.6,图5F)。肠道微生物不成熟与各种免疫疾病有关。正如研究中表明,大肠杆菌的丰富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下降到一个新的、较低的平衡状态。大肠杆菌丰度和肠道微生物不成熟之间的关联可能与其他更成熟的共生菌缺失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有关,这可能会影响免疫成熟。作为一种高度适应肠道的物种,大肠杆菌可以在生命的最初几天内在肠道定植,并且在物种内部具有显著的遗传多样性。许多共生的大肠杆菌分离菌可通过病毒性因子引起消化道疾病。然而,高ARG负荷对肠道成熟度的潜在作用尚不清楚。但毫无疑问的是,高ARG负荷会给这个物种带来更多的健康风险。
图5. ARG聚类、ARG丰度和大肠杆菌丰度对哮喘风险和肠道微生物群落成熟度的影响。(A)在两个ARG聚类中细菌PLS评分。(B)总ARG丰度对数值与和哮喘相关的细菌评分之间的关系。(C)大肠杆菌对数转化相对丰度与PLS评分的关系。(D)两个ARG聚类的MAZ得分。(E)总ARG丰度对数转化值与细菌成熟度(MAZ)的关系。(F)大肠杆菌相对丰度对数转化值与MAZ分数的关系。
在本研究中,我们综合分析了662名1岁儿童ARG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各种环境暴露、肠道成熟度、与哮喘相关的细菌之间的联系。我们证实大肠杆菌是1岁健康儿童肠道中一个极其重要的ARGs库。通过描述健康婴儿肠道微生物群中ARG的分布及其与细菌种类的关联,我们能够识别与不同门类的细菌相关的ARGs。我们分析了关键环境因子与ARG丰度的关系,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次将兄弟姐妹的存在、出生季节、家庭类型、宠物的存在、生活环境的类型以及怀孕期间抗生素的使用等因素与婴儿肠道ARG分布的形成联系起来。在这里描述的重要关联中,我们发现了儿童使用抗生素的短期影响和母亲使用抗生素对健康婴儿肠道中ARGs的影响。最后,我们揭示了婴儿肠道ARG丰度和微生物不成熟、与哮喘发展相关的细菌群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我们关于早期生活环境对婴儿耐药性的影响的发现可用于支持公共卫生预防,旨在减少病原体间ARG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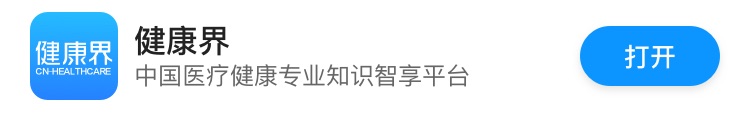




 打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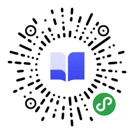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