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战“疫”的社会心理意义
友情提示:长文,慎读,而后慎独!
任何一种疾病侵袭的都不仅仅是肉体,还有人们的心理和心灵!
2020这个春节不期而至的新型冠状病毒带给病患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痛苦不言而喻,即使未被感染的“旁观者”们也能深深体会到个中之“痛”。
因此,这种“痛”不会仅仅停留在个体的肉体和心理上,而且深深的印刻在社会心理之中,是一种共性的社会之“痛”。
在这里,“德济心理”想从历史、文化和社会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全民战“疫”的社会心理意义。
历史上的战“疫”
195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约书亚·莱德博格(Joshua Lederberg)曾言:“同人类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就是病毒。”时至今日,此言仍然不虚,因为人类仍未研究出能够彻底消灭体内病毒的药物或治疗方案。

病毒是一种结构极其简单的生命形式,它们没有细胞结构,仅由核酸和蛋白质共同构成或仅由蛋白质构成。
生物进化通常遵循从简单到复杂的历程,病毒被认为是非生命物质到生命体的漫长转变过程中的一个中间过渡体。
从这个角度看,病毒在地球上的生存历史比人类这种结构极其复杂的生物体要久远的多,可谓最早的“地球霸主”。
但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类早已成为“同病毒争夺地球统治权的唯一竞争者”,或许正是不甘心于此,每隔一段时间,各色病毒们(天花、水痘、麻风、伤风、艾滋、SARS、流感、禽流感、新冠病毒等)便相继跳出来“踢馆”,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和深刻的警示——警醒人类善待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灵。

人类自诞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与疾疫的缠斗。
我们不知道史前文明是如何战“疫”的,但可以想见的是“互助”一定是人们战胜疾疫的不二法宝。
当然,每个部落中还有一个可以通“神灵”的精神领袖通过激发信仰和信念的力量来助力人们去战斗。

我国自有史以来发生过很多次大规模的疾疫事件。下图是邓云特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记录的自古以来影响力较大的部分举国性疾疫事件,总体呈上升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救荒史》,邓云特著
这与什么有关?
具体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还是在于人口的增长,加上城市化的发展导致人口密度增加,为疾疫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清代中后期以前,中国这片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大约为6000~8000万,人口总量一旦超出这个限度,饥荒、疾疫、战乱便会相继而至或同时发生,导致人口锐减。
01 古时:战“疫”
古时的人们在面对疾疫时从来都不是束手无措,很多积极的应对方法得以实施,包括以下形式:
一、国家的组织:封锁城池、采取“隔离”措施
自先秦、秦汉以来一旦发生了大规模传染病,国家首先做的就是采取封锁城池(现世简称“封城”),禁绝交通。
“隔离”措施最早可见于西汉末年《汉书·平帝纪》中的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后世亦有“六疾馆”、“疬人坊”等用于隔离感染病人的专门场所。
历史总会告诉人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隔离”这一古老的防疫措施在本次疫情防控战中再次被证明是有效的。

二、发挥科学的力量:置医施药、义诊、公共卫生、免疫接种
中医药无疑在古时的疫情防控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代的医者们也总是冲锋在前的最美“逆行者”。
《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师疾疫,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东汉末年的张仲景正是在亲身战“疫”的医学实践中编写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

宋元以后,科学的力量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有了更多的科学手段用于疾疫防治,如倡导个人卫生、发展公共卫生、开展有组织的义诊、安抚民众心理等措施。
至明朝隆庆年间,人工种痘免疫技术被发明出来,人们将天花患者的疱液和痘皮晾干、磨粉,然后接种在未感染过的人的鼻腔里,使其产生对天花病毒的免疫力,但这种方法不够安全,常导致接种者染上天花甚至死亡。

三、发挥社会的力量:慈善组织
自东汉末年以来设立的各种防疫隔离场所已具有官方慈善组织的性质,魏晋南北朝、隋唐、宋代由地方乡绅阶层或宗教团体(佛教机构)等民间设立的“悲田养病坊”、“安济坊”、“养济院”等机构则展现了疫情防控的民间慈善力量。
自明清之后,官方和民间设立的慈善组织如“善会”、“善堂”等则在大规模疫情防控期间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四、发挥文化的力量:文化习俗

古时人们限于对疾疫的科学认知水平,往往将其归因于超自然力量,加之当时的医疗水平远不足以应对各种疾疫,人们便需要在思想上寻求对健康和生命的寄托。
往往大规模疫情发生的时候,统治者们便反躬罪己、祈祷禳除,通过彰显敬天爱民的举动来祈求疾疫停息。
民间的许多文化习俗也出自古人应对疾疫的经验总结。
例如,重阳节登高最初便是出于避疫的目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发现瘟疫往往发生在人口集中的平原地区,因而在疾疫爆发时躲到山中,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个习俗。
过年时燃放的烟花爆竹最初也是用于驱避“山臊”这样一种可以使人寒热染病的鬼怪(《荆楚岁时记》、《神异经》)。
先秦时期的人们认为五月是“毒月”,尤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此时正值仲夏时分,毒虫、恶疾易盛。
因此人们便在当天佩戴香囊、门前挂艾草和菖蒲、喝雄黄酒等用以驱虫避邪(“邪”在古时被认为是诸多疾疫的“病因”),这其实是端午节最早的起源。
至今仍活跃在安徽、湖南、贵州、江西等部分区域的傩戏便是最早起源于商周时期的驱疫仪式,《续汉书志˙第五˙礼仪志》曾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此所谓大傩驱疫。

故宫博物院馆藏《大傩图》
或许,古人采用上述方式来应对疾病在我们看来并没有太多科学道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习俗作为一种文化适应性的战“疫”方式,无疑在当时的环境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护佑心灵的作用。
而心灵之与健康有多大的意义呢?意义太大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最新的健康概念——“全人健康”,即个体达到身体、心理和灵性(spirituality的常用译文,窃以为不尽恰当,易被误解为宗教相关的概念,或译为“心灵”更妥。此概念下文会有详解)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平衡状态。
也就是说,灵性(或称心灵)健康是等同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健康理念,能够起到护佑心灵作用的文化习俗和生活信念自然可以起到保护健康的作用。
简单总结一下古人战“疫”的大致情形:
政府组织/领导,民间力量共同参与、百姓互助、医学家们冲锋在前、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力量必不可少,这样的情形与当前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不无相似之处。
不过,我们所拥有的战“疫”力量是远非古时所能比拟的,而且根据古时疾疫往往兴于战乱、息于统一的历史规律,发生于和平当下的新冠疫情自当不会久远。
02 古人如何体验疾疫
疾疫在身,躯体和心理苦痛并行是必然的,但是苦痛体验往往还会超出躯体和心理层面。在此我们借用一些古诗词来共同感受一下。
躯体感受:“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李清照《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两鬓华》)、“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陆游《病起书怀》)、“归来骨薄面无膏,疫气冲头鬓茎少”(李贺《仁和里杂叙皇甫湜》)、“蓬鬓哀吟长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卢纶《逢病军人》)。
心理感受:“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醉,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韩琦《点绛唇·病起恹恹》)。

超脱出躯体和心理层面的感受——社会心理: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曹丕《与吴质书》)。
曹操所感怀的苦痛代表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而曹丕的痛既是代表对亡友(书中四人皆居建安七子之列)的哀痛之情,也代表了对于建安文学未来发展走向的担忧。
而对于大众百姓来说,“桐花入鬓彩系臂,家家御疫折桃枝”(白玉蟾《端午述怀》)更能代表普遍的社会心理——驱厉逐疫的美好愿景!

现代社会的战“疫”
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个体的病痛很容易通过各种传播渠道为他人所知晓和体验到,从而衍生为社会的“苦痛”。
这种“社会苦痛”不仅仅源于疾病本身的传染性以及由此引发的恐慌心态,还在于人人都可以感同身受。
因此,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全部的社会力量,包括预防、救治、援助、报道、生产等等,都被动员起来战“疫”。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人人自危、人人自保,更多的是人人互助。
谁获益谁买单是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疫情结束最终获益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那么全民投入战“疫”就是理所应当的。

01
影响社会心理的因素
疫情相关的信息披露、新闻报道,防控措施,防治成效,防治和支持性资源,各行各业的专业作为等均会影响到社会心理反应。
从群体层面来说,人类对一个未知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物产生恐慌心态是正常的心理反应,是人类一种原始的集体潜意识的传承,无需以太多的异常或病理性的视角来看待。
从个体层面来说,基础健康状态(身体、心理、灵性健康和社会适应状况)会决定个体的心理反应。
躯体健康的个体自身免疫力强,不容易感染病毒,心理上自然更笃定;心理上对不确定性的耐受能力较高的个体出现焦虑、恐惧心理的程度可能也较低;社会适应良好的个体,面临因疫情被打破的生活常态时更能积极的尝试开发生活新常态。

这里重点谈一下灵性(spirituality)健康对于疫情相关心理反应的影响。
灵性的现代概念指的是“人们如何理解生活的终极意义和价值”(The way in which people understand their lives in view of their ultimate meaning and value)。
简言之,就是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积极向上的“三观”可以使人在面临应激时能在更高水平上“自动化”调整躯体、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状况,从而保持应激反应水平处于可控范围。
而愤世嫉俗可能使人更倾向于关注负面信息或更容易对信息进行负面解读;固执刻板可能使人更难于适应生活常态被打破的局面;自私贪婪可能使人觉得更无助(因为帮助永远是“不够”的、永远无法被满足);斤斤计较可能会使人感到更没有安全感(因为总是不愿放过别人的人在困难面前也不会放过自己)……。
总之一句话,你是个怎样的人决定了你会怎样度过本次疫情!
02
疫情过后,心理问题会“井喷”吗?

不会!
首先我们要明白疫情当下的社会心理反应的实质是人们应对不确定性事物的正常的境遇性反应,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反应远未达到“问题”的程度,当疫情这种境遇消除后,相应的心理反应自当会很快消除。
其次,任何疾病最好的医学干预都是病因学干预,疫情的确可能引发一定的心理问题,可一旦这个病因学因素被消除了,剩下的心理问题也就好处理了。
另外一点,也不能太低估了国人的承受能力,有句老话说的好,“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
毕竟,中国人群的抑郁症、焦虑障碍的患病率都远远低于西方社会。
03
谁是最好的心理健康守护者?
奋战在防控前线的医务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各级政府和社区管理人员、坚守各自岗位的生产者、认真做好了自我防护——尽可能保持生活常态,或努力开发生活“新常态”的每一个 “我”,连同已经站立在战“疫”前线的精神卫生工作者们,都是自己和他人最好的心理健康守护者。

04
需要重点关注的社会心理:创伤的修复
这次大规模的疫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心理创伤,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绝大多数人都能顺利的完成创伤的自我修复。
而对于很多疫情亲历者们来说这种创伤是巨大的,创伤的修复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这些亲历者们包括,染病的患者、失去亲友的人们、虽未被感染但一度生活在恐惧环境中的人们、各条战线上的战“疫”工作者、牺牲生命的工作者们的家属等等。
如何看待他们的创伤?
面对生活的“无常”所带来的任何创伤体验都是人之常情的“正常”心理反应。
或许有人会出现抑郁症、焦虑症、应激相关障碍……的症状,或许少数人还会满足某种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但此时仅仅以疾病的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总是习惯于看到同一疾病标签下千篇一律的生物学或心理学后果,很容易让我们医生忽略掉更加显而易见的、同样应该是干预目标和帮助方向的家庭/社会性后果。
相较前者而言,后者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每一个亲历者在疫情期间的经历、他/她的人生经历、生活经验、生活环境和家庭背景都会掺杂到他们的创伤体验中,导致每一段创伤体验都是独特的,因而他们需要的帮助也是多元化的。
相信我们精神科医生不会把这些多元需求简化为处方笔下一颗颗跳动的小药丸。
如何处理创伤?任何支持都是有帮助的!
对于失去亲友的创伤,最好的疗愈工具是“哀悼”,这是人类社会在千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出来的最强大的创伤修复工具,对于任何一个文化群体来说都是如此,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而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很多哀悼仪式在现阶段是无法完成的。
待疫情结束,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层面一定都会开展一系列的悼念活动,去逐步修复个体和社会的心理创伤。
对于一些重点人群,精神卫生工作者们也会综合运用医学、心理学、人文(我们认为,“人文”在医学领域从来不是精神或情怀,而是实实在在的医学技术!)等等的手段来帮助他们。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很多起到护佑心灵作用的传统已渐行渐远,该如何回归呢?
当然,疫情结束之日也是我们开始思考如何放慢疾行的脚步,来静静思考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了。

人点赞

人收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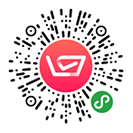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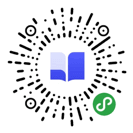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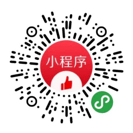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