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ICU医生的武汉“战记”:我淬炼成了“多面手”
作者:杨志明(浙医二院长兴院区重症医学科)
来源:健康县域传媒
疫情就是命令。作为全国第一个启动疫情一级响应的省份,浙江省迅速派遣了应急支援武汉医疗队,首批队员于大年初一便启程赶赴武汉支援抗疫。因为疫情凶猛,短短3天不到,浙江省又迅速集结组建了第二批援助武汉医疗队。我作为一名重症医学医生,接受了派遣,与省内其他各兄弟单位的同道一起,于大年初四火速出征武汉。
说起当初的决定,还有为什么会是我,其实很长时间里我也没能想明白。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这是一项充满危险的任务,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决定了,哪怕再苦再大的困难,我也要全力以赴去克服。
重症病床总是收得满满当当
我们是乘坐1月28日晚上的包机离开杭州萧山机场,经过约2个半小时的飞行,于当晚8点左右抵达武汉。初抵武汉,冷寂是我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除了我们医疗队队员和为数不多的安检人员以外,诺大的武汉天河机场几乎看不到一个乘客。
浙江医疗队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我们第二批援汉医疗队对口支援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属于第三批开放收治新冠病毒肺炎的定点医院。按照武汉市政府的部署,计划开放600张床位用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因为医院硬件设施跟不上,暂定开放350床,监护室病床10张。
疫情期间,医院腾出2015年新落成的19层住院大楼用于防疫,设置了10个隔离病区和1个ICU。在医疗队到达的前一天,勉强刚刚完成院感防护隔断施工。该院病房层流于去年10月到期未维护,病区仅有一间负压病房还达不到负压标准,其格局完全不符合“三区两通道”的院感防控要求。尽管存在种种不足,医疗队派出院感管理等专家督促并协助天佑医院完成了必要的整改。各专业组按时完成了上岗前的严苛培训,并于2月2日正式进入医院开展诊治工作。
我所在的重症医学专业组共由12名医生和48名护理人员组成。因人员相对紧张,医生工作时间实行“三班倒”。每班两个人,加上穿脱防护服、手卫生和往返时间,一个班次基本需要11-12个小时。常常是天蒙蒙亮就要出发,等到下班回到驻地,天色基本上都暗了。亦或夜班,晚上10点多出门,转天上午九、十点钟方能回到住处。
工作期间要求全程穿着防护服,不能吃喝及上厕所,并执行严格手卫生。尤其是脱防护服,每一步骤都必须手卫生消毒,脱一次防护服手卫生超过20次。从接管病房以来,重症监护床位几乎总处于满员状态,而且经常有其他病区或急诊电话打来要求床位。因为疾病传染性的缘故,不设家属陪护及探视,且没有护工,护理人员异常辛苦。
浙医二院长兴院区重症医学科杨志明工作剪影
陌生的工作环境,《危重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方案流程》的理论层面认知,临床经验缺乏,每个医护人员全程包裹在层层叠叠的厚重防护里工作,这一切都成为了首先需要克服的困难。
因为疫情扩大和前期长时间鏖战,天佑医院监护病房原有的大部分医护都撤出休整,只留有少量人员协助我们工作。很多医护都来自妇产科、外科,有些甚至从来没有在ICU病房工作过。他们现场学习呼吸机治疗、气管插管,深静脉置管操作。我们向他们学习如何使用电子医嘱病历等系统,以及如何与家属保持联系。
监护病房额定10张重症病床总是收得满满当当,并且常常会加1-2个床位。因考虑院感防控,每次只能有一名医生,三、四名护士在里面。医生需要查看病人病情、指导护理、呼吸机调节、气管插管、调整连续肾脏替代疗法、处理危急情况、乃至心肺复苏等等,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有些重症病人 最终还是没扛住
刚开始找不到北,经常晕头转向。这边病人突发氧饱和度下降未处理完,那边又喊心脏病人血压波动;一边上无创呼吸机的病人谵妄,氧饱和度低到不足60%,亟待气管插管;一边又有人喊,病人突然心率骤降……护目镜里已经开始起雾模糊,口罩已经开始湿了,防护服里的衣服已经湿透全粘在身上,手脚也有些笨拙。但是我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绝不能让病人因为我的失误而离去。
重症监护病房内护理人员与交接班
往往总是事与愿违。虽然我们奋力拼搏着,努力着,还是不断有病人逝去。刚开始的半个月,几乎每天都有1~2个病人抢救不过来,被双层尸体袋包裹着从病房里拉出去,黄色尸袋上大大的黑色“奠”字特别醒目,似乎在诉说着什么,但一切又是无声无息。
有一阵子,大家情绪都很是低落,特别是贴身照顾病人的护士,就好像是辛辛苦苦忙活了大半年的农家,原本期待有个好的收成,一场台风把庄稼全刮跑了,欲哭无泪。经常会有护士问我,杨医生,以后我们还是少插管吧,风险这么大,最后病人结果和没插管一个样。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是安慰:相信指南,相信我们的能力,按照正确规范的流程来操作,继续努力,一切会好起来的。
病人还是很满,但从二月中旬起,已经开始断断续续的,甚至连续几天没有病人死亡。终于有病人好转出去了,其中有一个是某企业的老总,年纪不大,50岁左右,发病到加重约10天,起初在普通隔离病房治疗,没有起色,病情越来越重,最后转来ICU,刚来的时候高浓度吸氧饱和度不足70%,一直给他做无创机械通气,大约坚持了10天左右,改为经鼻高流量氧疗,慢慢的改成普通氧疗,氧饱和度也不错了。
劫后余生,病人很感激,也许是切身体会到了我们的不易,转出去后让人一口气给医院捐了5台呼吸机和200副护目镜,着实让微信群里热火了几天。但是我知道,这还只是开始,真正的难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那就是有创机械通气着的那些病人——硬核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
当仁不让地做起了“超声科大夫”
这些被我们戏称为“全家福”的胸部X线照片,基本上都是最危重的新冠肺炎病人。这些也是我们了解病人肺部情况的最直接资料。在这里,因为穿着防护服的缘故,听诊器是无法使用的,而CT更是一种奢望。病人的临床症状常常和肺部实际情况不符合,不典型性,一旦加重起来变化很快,且没有转运呼吸机,病人的情况和院感防控条件都不允许。胸片并不能反映肺部情况的全貌,无法获知病人的心功能状况与血流动力学情况。而超声正好弥补了这些欠缺。
杨志明经治的新冠病毒肺炎危重症患者胸部X线摄片
重症监护室没有配备B超机,通过重症组负责人和院方沟通,借得一部便携式超声仪。我们简直如获至宝!医疗队懂得重症超声技术的医生不多,大多只是会一点点结果判读。因为我之前早已把重症超声技术应用于临床诊疗,因此当仁不让地做起了“超声科大夫”。
探查胸腹水、了解肺水肿进展情况及有无肺实变、基本的心脏泵血功能、循环容量状况评估、基础血流动力学评价、指导鼻肠管留置等等,忙活得不亦乐乎。
杨志明正在行床边超声检查、指导其他医生
自从医疗队接管以来,我们已将原先治疗方案进行了彻底革新。然而,第一阶段的治疗总体收获并不太理想。2月下旬,医疗队重症组的全体医师和护理骨干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总结分析前期工作中的不足和教训。作为重症组中ICU工作年限相对较长的医生之一,我也提出了一些看法:没有突然变化的病情,只有对病情变化的突然发现。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病情的极端不稳定性,我们必须加强对病人的病情掌控,更好的保持治疗延续性等。
守得云开见月明
2月28日,第一例行有创机械通气的病人撤机拔管成功。这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发热半月余。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十年,因新冠病毒核酸阳性转至天佑医院。刚开始在普通隔离病房常规治疗,病情未见好转,且持续加重。
病人呼吸困难严重,遂转至重症监护病房。我们严格按照指南用药,并先后采用无创机械通气,有创机械通气,留置鼻肠管行肠内营养等治疗手段,却仍不见疗效。长此以往,病人会合并气胸,循环障碍等并发症。我们只能再次复查胸片,重新评估治疗方案。
经过综合分析、权衡利弊,我们决定给病人实施肺复张。即使用特殊机械通气手段,让水肿或实变的肺重新张开,肺组织内重新保持充气状态。肺复张实施过程极为精细,操作不当可能造成严重气压伤,加重病情。因此,全员调动,紧密配合。这一次,我们经受住了考验。经过反复多次的肺复张,病人呼吸与氧合情况改善明显。
在武汉,虽然新冠肺炎新发病人总数比之前显著回落,但危重症病人数量仍然居高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医护人员的疲惫感与日俱增,一起战斗的兄弟姐妹们中很多人睡眠成为了问题…
路漫漫其修远。这个季节的武汉多雨,傍晚时分,抬头往窗外望去,雨后的天空仍显得有些阴沉,四下里有些寂静,但似乎听得见远处马路上汽车划过的声音,不,是车流……
2020-03-03 于武汉
杨志明

人点赞

人收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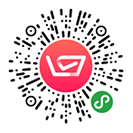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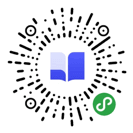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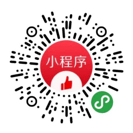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