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变迁与医药行业的新挑战
乍看之下,1812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创刊号与科学杂志的医学分刊几乎如出一辙————满是关于心绞痛的业内分析和研究婴幼儿腹泻、烧伤的文章。但事实上,这种与当今医学刊物的相似性掩盖了一种非连续性。因为1812年至今,医学界的敌手————疾病,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受到各种疾病的侵扰,医生们对这些疾病的看法各异,而各类疾病对社会而言也都有着不同的影响。要弄清过去200年间疾病在实质上与概念上发生的变化,就必须深入分析其社会属性。
疾病的发生、发展、定义和治疗往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实现的。首先,患者需要关于疾病的概念以说明自己的痛苦;医生需要关于疾病的病原学和病理生理学理论,因为这样才能对疾病做出解释,进而寻求治疗方案;决策者只有对疾病的决定因素和药物产生的影响有了客观的认识,才能制定出能够促进健康事业发展的医疗卫生体制。因此,上述相关人群的利益焦点以及医疗手段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都可以从过去200年间疾病的发展中找到极有价值的参考因素。
流行病的演变
文献研究发现,除心绞痛、痢疾和烧烫伤以外,早期的医学期刊关注的范围还包括枪弹造成的伤口、脊柱裂、法洛四联症、糖尿病、疝气、癫痫、骨髓炎、梅毒、癌症、哮喘、狂犬病以及尿道结石等。当然,其中的部分疾病至今仍在流行,而另外一些文章中描述的疾病则不太容易与当前的某种疾病对应起来。
卒中(apoplexy)是一种短暂性的意识丧失,大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中风(stoke)、癫痫发作(seizures)或者晕厥(syncope);但是在当时,人们对它的理解是:由于头部受到胃的影响而发生的神经“错乱”。
根据1812年医学期刊的记载,当时的医生发现如有炮弹擦过,即便不被击中也会指认粉碎性骨折、失明甚至死亡。还有早期的期刊反映,当时的医疗工作者对于过量饮酒者发生人体自燃的现象也有所关注。此外,发热也是早期医学期刊关注的焦点之一。1811年刊登的死亡统计表中不仅包括常见病因造成的死亡,而且还涵盖了特殊病因致死的记录,其中,肺痨、痢疾和肺炎是主要的死亡原因,但同时,出牙、蠕虫感染甚至饮用生水也都造成过人员死亡。
一个世纪之前,医学界根据具体致病菌对早期期刊所记载的传染病进行了重新命名,比如“肺结核”“淋病”和“梅毒”就是专家根据1912年期刊的主要疫情报告进行重新命名后得来的,除此之外,此外,还有白喉、麻疹、肺炎、猩红热以及伤寒等。马萨诸塞州的Penikese岛至今还保留着一个麻风病人隔离区,该隔离区早在1912年的文章中就已有记载。
热带地区的传染病也是当时的医学专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主要的病种包括在英国在热带的某些领属国内的移民中多见的蠕虫感染和鼠疫、黄热病和疟疾等。
1912年,医生们确实是有理由欢呼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之前的一年算是有资料记录以来健康史上情况最为乐观的一年。几乎每期医学期刊都会有一位百岁老人的记录,还有关于当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美国不同种族运动员取得巨大胜利的相关消息。有篇社论在总结当时的健康成就时甚至提出“或许到1993年,所有可以预防的疾病都将被根除,癌症也将被攻克,优生学的普及甚至会是‘优胜劣汰’的进化规律作废,而我们的子孙在回顾这些刊物时会倍感荣耀。”
然而,伴随着欢呼和赞美而来的,还有人类对于疾病不断“现代化”的担忧。1912年某医学期刊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种新的疾病,叫做“膝盖退化”,对部分人极度懒惰的生活方式提出批评;文章提到:“人们如今的运动量仅限于从房间出来到进电梯的步行距离、从电梯出来到休息室的距离以及从休息室再到车上的距离。”
当前,人为限制生育导致的种族渐进性灭绝,以及优生学的种种因素都开始日渐唤起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癫痫、酗酒、智障等问题的担忧。医生们也开始同癌症、子痫、阳痿、心脏病(尤其是感染性心脏病和心脏瓣膜疾病)以及关节炎等疾病做斗争。20世纪医学史上,心脏病、癌症和其他慢性疾病的地位尤为突出,不过期间也有诸如马脑炎(1938年)、苦鲁病(1957年)及大叶性肺炎(1977年)、艾滋病(1981年)、耐多药肺结核病(1993年)等传染病的爆发,此类疾病提示人类应提起对微生物感染的警惕。
疾病的定义与发展后果
疾病的实质性和理论性动态向人类社会提出了以下挑战:到底该如何定义疾病?人类该如何衡量疾病的负担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健康政策?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则极具迷惑性。韦氏医学词典对“疾病”的定义是:动植物机体正常生存状态的损伤。
那何为“正常状态”?如何定义“受损”?单纯借助生物学概念的话我们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因为对于“正常”和“病态”的界定需要一些价值判断。医生都知道,并非所有的症状都构成某种疾病。同时,能否简单地将医生诊断出的“疾病(disease)”与患者所经历的“疾患(illness)区别看来,人类学家对此提出了质疑。与之同时代的“酗酒”“慢性疲劳性综合症”和“精力集中障碍”等争议性概念而今已厘清,但“疾病”的定义却始终是个困扰医学界的难题。
负责任地讲,任何人想要给“疾病”下一个定义都必须要考虑该现象的复杂性。一种疾病既表现有体征又有症状,患病的通常为某特定人群,而且要经历一定的病程。医生要给疾病命名,探寻其病因,同时需要研发能够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手段。而病人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如何解释疾病给人类带来的负担
不管选用何种度量标准,对于疾病负担的描述都要涉及人群之中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其中有两个方面尤其让人烦恼,一是流行病随时间的进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二是健康状况失衡问题的不断持续。
通过对过去两百年间出现的各种新疾病的研究,历史学家对疾病的发生渠道进行了大致地归类。研究发现,新型或者非典型诱发因素、新的行为因素甚至新的治疗方法都能够导致新型疾病的出现。具体来说,新的诱发因素包括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交通事故、辐射所致的中毒;新的行为因素如吸烟、静脉用药等;至于新的治疗方法带来的疾病,胰岛素治疗造成的糖尿病病程和临床表现的变化可以算作一个典型例子。
随着环境因素和社会生活因素的变迁,以往的某些疑难杂症(如心肌梗塞、肺癌、苦鲁病以及疯牛病等)发生率可能提高。新的诊断技术和治疗手段可鉴别出以往难以辨别的疾病,如高血压;新的诊断标准也可以将某些疾病的范围扩大;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之下,疾病的判别标准也在发生变化,如同性恋、酗酒、手淫等,在过去的社会语境下被定义为疾病,而新的社会语境下则不再被划定为疾病。
还有一些新疾病的流行可能源于相关团体有意识的推动,艾滋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疾病的发生、诊断和影响都绝不仅仅是单纯的生物科学过程。一种新疾病的爆发通常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相关过程,因为这些过程一方面不断对流行病学进行改造,另一方面也影响着人类对疾病的理解和反映。
就疾病的衰退趋势而言,生物学和社会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都非常明显。1812年期刊上频繁提及的炮弹炸伤(connonballinjuries),在当时人们看来是令人极为忧心的健康威胁,而最终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令人恐惧的战伤报道。再如,神经衰弱(Neurasthenia)在19世纪晚期曾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神经系统疾病,后来关于该疾病的文章逐渐消失,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该病的相关记载对于很多其他疾病的诊断都颇具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一种疾病的衰退则是某种医疗手段的直接结果,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的根除就得益于免疫接种。根据2009年的文献记载,基因筛查使得很多先天性疾病大规模减少。
尽管流行病发生了变化,但健康资源的失衡依然存在。不管健康的测量标准或测量人群如何变化,健康状况的不平衡状态都始终存在。欧洲人刚刚到达美国时,他们就对欧洲人、土著美国人和非洲人之间的显著的健康差异做了观察。19世纪工业革命后,医学界也发现了贫富人群之间的健康水平差异。而健康水平的差异不止存在于种族、民族之间,更与地理因素、性别、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以及其他因素紧密相关。
持续存在的健康差异对医学界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但如果深入思考此问题的解决方案,人类也将受益良多。
药物的角色
一切医疗错事和健康政策的制定都有一个前提,即疾病是可以被医生及其治疗方法攻克的一个问题。20世纪的医药史是医生借助生物医药的发展来争取保健和延长寿命的一段历史,然而这段复杂的历史中充满了人类与疾病之间的激烈抗争。
比如,1882年罗伯特·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以及1940年抗生素的问世,医生称其在抗击欧洲和北美流行的结核病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结核病在欧洲和北美的减弱趋势早在科赫发现结核杆菌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而且在对抗结核菌的有效抗生素问世前,结核病例就已经开始大幅度地减少。于是,医学评论家者转而又将此归结为生活质量特别是饮食的改善。同样,冠状动脉疾病也引发过类似的争论。同结核病一样,心脏病也曾出现长达一个世纪左右的流行期,并在流行近50年后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美国达到高峰期。2007年的一份医学研究报告中,研究者曾质疑,对于上述疾病流行趋势的衰减,很难绝对地说在多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医学工作者的努力,而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疾病危险因素本身的减少、此类争论如今在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冠脉病领域仍然存在,并且呈愈加复杂的趋势。随着当前健康资源配置的竞争日益激烈,此类讨论无疑是更具影响力的。
那么,所谓的“最佳的健康政策”究竟是否存在呢?我们需要的应当是一种综合性的健康政策,以确保各项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项目能够协调运作,共同解除疾病带给人类的沉重负担。但该政策的具体细节则在于我们如何定义和衡量疾病的概念。此外还需考虑到的是,疾病并非一种长期处于静态的事物。正如生物体为适应周围环境而不断进化一样,为了对抗日益升级的疾病,医药行业工作者也需要做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由于医疗的革新需要时间,因此尽管医学家们找到了解决某些疾病的办法,但是疾病带来的负担只是发生了变化而并未消除。比如,医学家发明出抗生素和疫苗来对抗传染病时,疾病的负担便转向了癌症、中风等非传染性疾病造成的高死亡率。医学界努力研究出能够对抗或攻克此类疾病的成果后,疾病对我们人类的挑战却又转向一个新的领域。比如神经精神病学的疾病业已成为一个新问题,但目前尚未有效地治疗办法。
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我们的现有医疗体系对于过去的疾病种类来说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它却不能很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的疾病体系。因此,我们需要继续调整和推进当前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卫生政策,以适应不断演化的疾病。
但是我们要做的还不止这些。疾病是人类的生存体验中一个复杂的部分,作为医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复杂性,进而规划出相应的措施和论体系以全面地阐释疾病这个概念的广度和细微之处。
(原文出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原文作者:David S.Jones)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不感兴趣
看过了
取消
精彩评论
相关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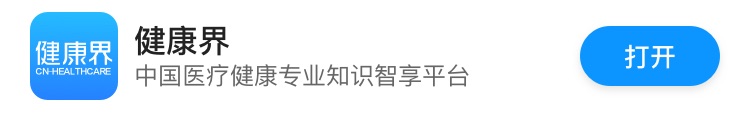




 打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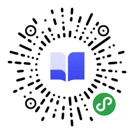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查看全部条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