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生死之间,只隔着一个口罩
作者:小小强
来源:医殇
不以为然的现实
据武汉市卫健委2020年1月5日最新通报,截至当日8时,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7例。目前所有病例均在武汉市医疗机构接受隔离治疗,已经追踪到163名密切接触者并行医学观察。
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刚挤进北方早高峰地铁的人缝里。人群中不时传来的咳嗽和喷嚏声,让我一次次下意识地将医用外科口罩的鼻夹金属条紧了又紧。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一个同事的8岁女儿被确诊支原体肺炎住院治疗,另一个同事的6岁女儿发热39度确诊甲流(在她发热、确诊之前,已经因班内相继确诊几例甲流而停课在家)。
不管是古老的肺结核,还是2003年第一例“非典病人”;不管是2019年11月北京的两例输入型肺鼠疫,还是幼儿园、小学每年“司空见惯”的支原体肺炎、流感……,防控措施的核心不外乎以下三条: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呼吸道传染病通过患者咳嗽、打喷嚏时喷出的口、鼻分泌物而传播、感染给下一个易感者。在大众所接受的教育里,综合性预防措施包括:开窗通风、勤洗手、避免到人多拥挤的公共场所......但一代又一代,很少有老师和家长告诉下一代:如果我们无法避免去公众场所,我们应该及时、正确地佩戴口罩!
记忆中,十几年前SARS肆虐时,口罩供不应求。
现实中,口罩涨价是在近几年北方的雾霾天。
但在没有SARS、没有雾霾的日子里,除了医院里的大部分医护人员和大街上的部分清洁工人,即使是我们成年人,也不屑提高安全健康意识,用口罩去保护自己,更没有公共卫生意识去保护家人、保护其他身边熟悉或陌生的人。
每天挤地铁、公交上班的人,从呼吸体验和经济成本出发,不可能为了预防呼吸道传染病,而每人每天戴个口罩保护自己。
但已经有咳嗽等呼吸道疾病传播风险的“传染源”,还是应该在公共场合委屈自己随身携带和适时佩戴口罩,借此通过主动切断传播途径而保护下一个易感者。这样的公共场合应该包括但不限于:医院、密闭的公共交通工具、教室、办公室……尤其当我们面对老人、小孩和孕妇。
某种程度上,呼吸道传染病患者在公共场所主动戴口罩,与公共场所禁烟,对保护无辜的易感人群而言,殊途同归。
不堪回首的往事
SARS爆发的第二年,大学暑假,我和同班的老乡从中部的火炉城市提前预定火车票返回北方家乡。出发的前几天,我在图书馆的空调旁爽快了一上午。记忆中,那个老图书馆里的立式旧空调运行没几天(按后来所掌握的知识,里面应该寄居了不少致病微生物)。当晚开始,高烧、腹泻、咳嗽接踵而至,但还是硬扛着盼到出发前“病情好转”,最终一路咳嗽着靠一张18小时的坐票抵达家乡省城。
在家乡省城的表姐家寄宿的当晚,收到了火车上同行的同学到家后高烧住院的消息,我暗自内疚,意识到是我一路咳嗽传给了坐在对面的她,至于当时坐我邻座的另一个陌生女孩有没有幸免,不得而知。
即便如此,我依然在怀有身孕的表姐家住了下来,直到后来回到县城后得知,她一度纠结于孕期该不该吃药治“咳嗽”。我再一次深感自责,直到外甥安全出生。
再一次亲历呼吸道传染病的凶险,是在7年前,两岁的儿子确诊白血病,在国内最大的血液治疗中心化疗的那三年。
因为某种历史发展的原因,治疗技术的国内一流与病房环境的陈旧拥挤,对于这些免疫力低下的血液病儿童,既幸运又残忍。
环路的东边是宽敞明亮的金融街商务办公楼,环路的西边是一床难求的一个个六人间(加床的时候,含陪护家属,每屋每晚多于12人)。
每个接受化疗的小孩都应该在病房里把口罩当作不可或缺的护身铠甲,但不是每个年龄段的小孩都懂得口罩对他的现实意义。每个在病房陪护的家属都应该把口罩当作保护自家和别人家孩子的盾牌,但不同背景的成年人未必有同样的危机意识和利他情怀。
化疗间期回到家里,每天在外奔波谋生的我,在外碍于情面、在家心存侥幸,并没有把口罩上升到“关系孩子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跟孩子密切接触时,毫不设防。
三年化疗期,孩子相继发生过病毒性肺炎、支原体肺炎(一度因肺实变而出现鉴别困难)、绿脓杆菌败血症(肺炎、脓胸,监护室两进两出)。如果说败血症可能是院感相关的血行感染,那么没有争议的事实是,病毒和支原体应该是通过呼吸道传播。至于呼吸道传播的场所,可能是病房,可能是家里,也可能是其他公共场所。
三年化疗,预计花费20万,却因三次肺炎,实际花费50余万。以至于三年化疗停药后不幸复发时,为了减少骨髓干细胞移植期间呼吸道传染病的罹患风险,毫不犹豫舍近求远去了另一家移植技术和病房环境都不错的医院。
骨髓干细胞移植后四年半,一路坎坷,免疫力比化疗期间更低,免疫力恢复更慢,但侥幸的是,期间没有再发生重大的呼吸道传染病(按照长辈们的忌讳,这段话应该省略不说)。
吸取三年化疗期间的惨痛教训,移植后的四年半,只要迈出家门,孩子逐渐习惯了自觉戴上口罩。不管在晴空万里的盛夏,还是在雾霾笼罩的寒冬,地铁里戴着口罩的我,也并没有因为周围是否有人戴口罩而怀疑自己是否另类。至少,身处公共场所时,戴着口罩的我们,不至于因旁人的一声咳嗽或一个喷嚏而无所防备。
不敢奢望的未来
真心希望,如武汉卫健委通告所说: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武汉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暂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也真心希望,武汉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有如2019年11月的北京2例输入型肺鼠疫一样,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层面,有惊无险。
而于我们每个个体而言,口罩的现实意义不应该只是防SARS防霾,而应该还包括所有曾经被忽略的跟“飞沫”或“吸入”相关的疾病防控。
每一个医护人员应该站在院感防控的角度用口罩保护自己、保护易感人群。
每一个清洁工人或粉尘作业人员应该站在比“养家糊口”更严峻的角度去保护自己的呼吸道。
每一个身处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期的成年人,都应该有意识地利用口罩去减少疾病在公共场所的进一步传播。
每一个坐在教室的学生,在不幸感染呼吸道疾病但尚未达到停课隔离标准时,都应该在老师的引导和家长的配合下,利用口罩去保护自己的同桌。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个白血病儿童的父亲一样,不戴口罩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大多数人的切身感受应该还停留在戴着口罩呼吸不畅快。
从阻止疾病传播的角度,口罩和安全套的发明,其实具有同等意义。适时携带和正确佩戴口罩,应该和安全套的使用原则一样,既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他人。
有固定性伴侣的健康人,如果不是避孕的需要,从预防性传播疾病的角度,并不需要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
但明知自己有呼吸道传染病,却在家里或公共场合与他人面对面时不戴口罩,任由自己咳嗽的飞沫飘进别人的鼻孔,跟那些明知自己有性传播疾病,但在家里或外面跟固定或不固定的性伴侣接触时不戴安全套,任由下一个无辜者跟你一样遭受不幸,从道德层面讲,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口罩,戴与不戴,主观的舒适体验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相对而言,真正意义上的舒适应该是:自己安全,别人也安全。
在免疫力无法快速恢复的当下,在这个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移植后四年半的儿子依然不敢迈进校园体验集体生活。
未来如何,不敢奢望。
改编一首流传于网络的《霾愁》,苦中作乐:
古时候,
口罩是一个小小的道具,
我在这头,
强盗在那头;
小时候,
口罩是心中深深的恐惧,
我在这头,
针头在那头;
再后来,
口罩是2003年的集体记忆,
我在这头,
SARS在那头;
现如今,
口罩是全民的防霾神器,
我在这头,
却看不清,
谁在那头......
而对于一个免疫力低下的男孩来说,
口罩不是《我不是药神》里的道具,
而是他得以幸存的护身符
生的希望在这头,
死神的獠牙在那头。

人点赞

人收藏

打赏






















 010-82736610
010-82736610
 股票代码: 872612
股票代码: 8726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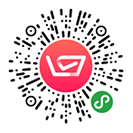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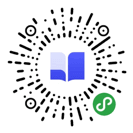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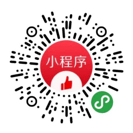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0745号






